一柄剑能改变什么。
在童话故事里的话,是整个世界。
它被赋予了魔力,自人类创造出这种有着修长切割刃的美丽武器时起,它们就时常被寄托各式各样的理念,成为某种化身。
但现实没有那么天真,一柄剑到头来。
也许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拯救不了。
连那唯一的一个约定好了要守护好的对象,也没办法救下。
斩杀暴君吧,他说,他曾信,将暴君斩杀这一切混乱就会结束了。
可希格苏蒙德一世死了,尽管不是他亲手所为,关系却也密不可分。而东海岸在那之后却因为无主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罪恶的根源不来自于暴君本身,而来自于滋养了暴君的人民。”
“贪官污吏与蛮横的贵族固然可憎,但他们却并非从空无一物之中生出。助长了这种行为的正是人民的默不作声与逆来顺受。”
那时的她是这么说的:“农民起义、小国反抗大国有本身悲剧性的必然定律存在。多数时间我们并不祈求一切改变,而只是反抗了那一个掌权者或者掌权集团,希冀能有更加有为的人待在那个位置上。”
“这只不过是从一个奴隶主换成一个更加和善的奴隶主罢了。”那时的她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人民的全盘觉醒,从上到下的意识形态改变,不再懒惰不再逆来顺受不再默不作声。”
“这将会花上很多很多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数百年过后这一切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毕竟实在有着过多的阻碍。”
“不愿看到这一切发生的掌权者阶级会尽一切能力阻碍人民的意识形态发展,不光是贵族,即便是其它有权有势的阶级也会是如此。但最为重要的,却还是人性本身的怠惰。”
“我们总倾向于放弃独立思考将一切全盘交给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服从命令来行动的话活着也会轻松很多。”
“这是人性当中自然存在的奴性。”
“要改变这一切,将会是一个无比漫长又艰苦的过程。”
“但我们又何妨做最开始的垫脚石呢——”她说,她笑着说。
那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她的理想破灭了。
随着那仅有23年的短暂人生一并,潦草地、随便地、仿佛是神明开的玩笑一般就那样结束掉了。
像是其它不计其数的曾有志要改变这世界的人。
但区别于很多人,萨妮娅的身上有一种东西存在。
那是。
倔强到即便连面对死亡都不肯屈服的。
意志。
它与某种东西产生了共鸣,某种在血腥混乱的战场之上悄悄蔓延的东西。
于是。
连死亡也被克服了。
可这是她所期望的模样吗?
“这是你的理想所呈现的模样吗?”紧握着手中的克莱默尔,海米尔宁以那双灰蓝色的眼眸直视着整个帕尔尼拉的废墟。
遍地都是死尸。
绝大多数是那些有着黑色角质层外壳的食尸鬼,还有少数是全副武装的精灵、矮人、侏儒和兽人精英部队。
德鲁伊调动过来的精英部队。
若非他们的存在只怕这个暗处生长的帝国早就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东海岸。
魔法师们趋之若鹜的高等魔法在这片战场上随处都是,强而有力的火焰、冰霜还有雷电在半空之中接连闪现。
夹杂在这之中的人类十分无力,像是孩童在看着巨人争吵一般,连要去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都十分困难。即便是这些身经百战的大剑士,在这种规模的冲突面前也显得柔弱不堪。
但是正如在争斗巨人身下卑微渺小的孩童一般,他们也有着自己的优势。
“食尸鬼没有智力只有本能,它们的五感其实都已经大幅度退化,但是在脑部有着新的感官,可以侦测个体的强大程度——换而言之,魔力的量。”
“德鲁伊成员只要出现就会像是在一群鲨鱼里头投下了一块带血的鱼肉,但你们不同。”
“因为魔力低下的缘故,你们可以靠近到很近的距离都不会引起大范围的连锁反应。”
“换而言之,它们无法以这种敏锐的感官来察觉,只能用和老鼠一样糟糕的视力和同样糟糕的听力与嗅觉来感知你们。”
“计划是切成两支部队。德鲁伊的大部队在前面引开绝大多数的食尸鬼。而你们则凭借自身几乎可谓隐身的优势,在不引起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斩杀重点地区残留的食尸鬼。清出一条不会引起警报的安全通道供我们靠近——听起来很笨,做起来也很苦,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案了。”
“这样的话调集更大规模的军队不才是正解吗?”
“少年,人数多起来聚集在一处的话,即便个体的魔力量十分低下,总数高了超过阈值的话也会引起注意的。”
“这是孤注一掷的方法。一旦有哪一个环节走错的话就会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被群起而攻之的话我们也会招架不住的。所以唯一能够庆幸的东西只有它们没有足够强的组织能力,而为了进一步地确保这一优势。”
“我们必须去直面那唯一一个可以指挥所有食尸鬼,以自己的意志令它们行动统一划分的存在。”
“解决掉那个存在的话,剩下的食尸鬼就只是无头苍蝇,会因为被魔力吸引的本能而轻易地就掉进陷阱,是很容易解决掉的。”
“只是为此。”
“我们必须去直面她。”
“事情或许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想撤的话,现在还不晚。”艾莉卡瞥着海米尔宁如是说着,而后者迟疑了片刻,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出发吧——”
“锵——!!”克莱默尔挥过,硬质的角质层尽力阻挡大剑的锋刃,但食尸鬼的头颅仍旧冲天而起。
黑色的体液洒落在地上,但在精灵魔法师的大规模法术之下一挥洒到空气之中就立刻被烧毁。
不仅如此,地面似乎对于这些丑陋的怪物也是滚烫的,经常可以看到它们显得痛不欲生的模样。
若是没有魔法师的支援的话,只怕这一切会困难上许多。
“噼啪——轰——”雷电和其它魔法声响已经近在咫尺,热浪一阵一阵地从破败的房屋废墟之中传来,空气中的静电让众人的毛发竖起一不小心甚至行动牵扯到衣服都会被电到。但这样的事情身处激烈的战斗之中他们即便感受到了也会选择忽略掉。
“去吧。”前方就是帕尔尼拉的镇中心广场所在了,只剩下30多人的大剑士队伍当中的盖多回过了头,深深地看了海米尔宁一眼。
接下去的道路他应当一个人走,而余下的那些所有人就要在外面拼命拦住这些食尸鬼不让他们靠近。
宛如隐身一般的优势只能持续到现在,当作为中心点,作为这些如同“工蜂”一般的食尸鬼领袖的那只“女王蜂”受到袭击的时候。
它们。
会立刻团结起来,回防。
所以在这之前,他们必须解决掉她。而外围的大剑士还有德鲁伊的大部队目的就是拼命阻拦这些食尸鬼的回归。
可以预见到这会是一场血战,不论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
“嘭——轰!!!”外围电光和火光接连响起,踩在广场废墟之上,一共十三名高阶的德鲁伊精英成员走了进来。
他们正是以红牌佣兵的身份行走在人类社会当中的十三个人,从各族选出来的最精英最年轻有为的成员。
但包括艾莉卡在内这些在海米尔宁等人看来,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德鲁伊成员此刻却都是灰头土脸。“吼————”远方坠落在地上的白龙再度发出了咆哮声,显然受伤坠落的鲁密祁此时也仍旧在与食尸鬼奋战。
但这不是他们应当关心的事情,若真的要帮上那些正在奋战的同伴的话,最应当做的就是尽早结束战斗。
“.......”
一共十四个人,悄无声息地围住了整个广场。
广场中心的萨妮娅坐在一棵树下,正在看一本不知名的书。太阳将要落山了,在进入帕尔尼拉之后,杀到了她的面前又花费了他们一整天的时间。
“......”艾莉卡朝着周围开始打眼色。
夕阳落在了萨妮娅的身上。
刹那之间,海米尔宁迟疑了。
那安详又美丽的脸庞在这既视感强烈的光景下,一如许多许多年前的那个夕阳一般。
仿佛从那天起她从未改变过。
“也许我们还可以跟她,谈谈——”开口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他就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叹了口气。
“要想退缩的话,现在还不晚,乘船往东或者往西,你总归能逃离这一切。”艾莉卡冷冷地看着他。
“.......”海米尔宁握紧了手中的大剑。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一往无前,已经做好了决心要亲手结束这一切。但在看到她的一瞬间这份决心却如同海潮面前沙子做的城堡一般——空有坚不可摧的宏伟外形,实际上不堪一击。
“听着。你不清楚魔女可以做到些什么,你的内心动摇会成为她的工具。如果你无法下定决心的话,海米尔宁,你最好抽身离开,不然你会反而变成我们的敌人——”艾莉卡强调的下一段话被某人所打断:“阿丝特瑞娅,她——”一名侏儒的工程魔法师对着艾莉卡这样喊道,但她所称呼的这名讳却是海米尔宁所陌生的。
“她动了!拉‘,西‘,你们两个抑制住魔力。尤芬利克苏木和阿苏维持屏障,余下的人跟我上。海米尔宁——你到底怎么打算。”艾莉卡回过头对着他开口喊着。
“我——”海米尔宁短暂迟疑,然后看向了手中的大剑。
“啊啊啊——我早跟你说过你的优柔寡断迟早会害死你自己!”艾莉卡气得直跺脚紧接着转过了身一横长矛,电光“噼里啪啦”地闪烁,紧接着两名个子矮小长着尖耳朵金头发仿佛缩小版精灵的侏儒工程魔法师将某种器械安装在了地上。配合两名精灵的魔法运用,强大到连空气都为之凝滞的魔法被升了起来。
某种强大的冲击波以锁链的形式包围住了场中心的萨妮娅,精灵和侏儒的德鲁伊战士们维持着禁锢法阵,而其他人则是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活准备与已经被控制住的她进行战斗。
这看起来完全像是仗势欺人,声势惊人的这十三名德鲁伊的精锐占尽优势,海米尔宁根本没有插手的份,而被他们所包围的萨妮娅看起来是那么地柔弱,那么地楚楚可怜。
楚楚可怜,却又处变不惊。
“啪——”地一声,她合上了课本,然后将那有着修长弯卷睫毛的眼睛抬起来。
露出了一个微笑。
那即是海米尔宁所见到的最后景色了。
“天啊——”魔法的锁链碎裂,紧接着器械爆炸开把工程魔法师也卷了进去。精灵魔法师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兽人的战士手持海米尔宁根本无法搬动的巨斧咆哮着一跃而起,紧接着被透明的某物所击飞。在狂风将要到来的前一秒,海米尔宁听见艾莉卡微微颤抖的声音:“把白雪击落的攻击不是碰巧,她已经是——”
“完全体——”
“嘭轰!!!!”
眼前的世界被抹消了。
树、房屋、地面,还有周围所有的德鲁伊精锐全都不复存在。
“咚——!!”海米尔宁的后背狠狠地撞在了周围废墟的墙壁上,他立刻感觉到一阵痛楚,紧接着是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当锵——”大剑克莱默尔掉在了地上,在陷入视野逐渐模糊陷入一片漆黑之前。
他看到她。
缓步走了过来。
————
————
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稻草的杆子随之轻轻地拍动着脸庞。
秋日不甚强烈的阳光洒在身上,透过亚麻上衣和绑腿布带之后只剩下暖洋洋的感觉。
“海米尔宁——”
“海米尔宁!”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他睁开了眼睛,一张有着漂亮翠绿色眼眸的脸庞凑在很近的地方。她的左眼眼角有一颗泪痣,因为头上戴着遮阳帽的缘故向下的脸庞处于阴暗之中,但他仍旧能够看到对方皱起的眉头。
“啊——”海米尔宁抖了一下。
“你是不是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啊!”他“咻——”地一下坐了起来:“糟了,现在已经几点了!”
“只剩一个时辰了哦。”女性叉着腰这样说这,而海米尔宁赶紧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那我出发了!”
“路上小心点!”她在身后大声地喊着,而海米尔宁回过头用力地挥着手:“好——的——”他拉长了音调说着:“妈——妈!”
她压低了草帽,好气又好笑地摇了摇头。
充斥着痛苦和不情愿的某个声音,沙哑地响了起来。
“咦——”他停下了脚步,但身后却空无一物。
“睡迷糊了吗。”海米尔宁摇了摇脑袋,继续专注于眼下迫切的事情。
“哦唷哦唷,是小海米尔宁。”“婶婶好,阿姨好。”如风一样跑过镇上道路的少年一边用很有活力的声音和周围的大人们打着招呼,一边朝着小镇入口的方向跑去。
“老爸!”“哦,要出发了吗!”远方正拿着书本在指导镇民的书记朝着这边摆着手,他灰蓝色的眼眸之中满是笑意,而海米尔宁回头喊话的时候也没有停下脚步,因为这个动作不看路的缘故一头撞上了什么人——
“呃好痛——”他一屁股摔在了地上,然后抬起头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满是威严长着一对剑眉不苟言笑的面庞。
“希格苏蒙德大人——”海米尔宁抖了一抖,而对方那严肃的脸庞靠近了过来。
“.......”少年吞了一口口水,正担忧要迎来什么责罚之时,对方却忽然露出了笑容。
“你这小子,看在今天特殊的份上就不罚你抄字了。但是别的惩罚还是少不了,比如这个!”他用强而有力的双手叉着腋下把海米尔宁整个人抱了起来。“停下啦,爷爷,这样好丢人的,我都岁了!”满脸通红的少年挣扎着,但老人只是哈哈大笑着凑了过来用胡须故意去蹭着他的脸。
“称呼又忘掉了,是希格苏蒙德大人,或者校长大人。亲爱的海米尔宁一年级生!”
“好了,我真的快赶不上了,爷爷。”他依旧挣扎着,而围过来的镇民们都是微笑着看向这边。
“好、好。”对方放下了他,而海米尔宁一踩上地面就跑了起来,一边往前跑着一边回头挥着手:“我出发啦!”
“宝贝孙子也要长大成人了啊。”身后的老人抹着眼角,而也走过来看着那个背影的海米尔斯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还久着呢,接下来的道路上我们能教他的东西还有很多啊。爸。”
他们的这番话海米尔宁已经听不到,他只是往前跑着,沿途继续跟大家打招呼。
“今天要进行的字母的发音——”“修女大人好!”“啊,小海米尔宁,要出发了吗——!”修道院的修女正在教导孩童们知识,而她也予以海米尔宁祝福,令他感觉下脚更有几分力气。
他踩着石板一路往前,气喘吁吁地终于跑到了镇口的方向。
“哈——哈——哈——咦?马车还没.......来?”
“大家都.......”撑着膝盖喘气的海米尔宁回头左右观望,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在。
“你被阿姨骗了吧,海米尔宁·安里孔。”身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她知道你肯定跑去午睡就要睡过头,所以提早叫醒你了。”
“啊,妈妈真是个坏心眼。”海米尔宁整个人都焉了过去,无精打采地向着身后过来的那人竖起了手:“你好,萨妮娅。”
“嗯。”萨妮娅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夹在腋下的书本和海米尔宁一起坐在了村口的长条石凳上。
“真是,明明大家都这么悠闲。”“毕竟今天是开学的日子,你的行李呢?”马车尚未来,打开了书本的萨妮娅跟海米尔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托利卡多前辈帮忙带过去了,他们八年级的提早开学。是爷爷的主意,毕竟你晓得,我总是丢三落四的......”海米尔宁有些不自信地叹了口气:“亏父亲还给我取了安里孔这个二节名,但我却一点都不可靠稳重啊......”
“又有什么不好的嘛。”萨妮娅微微一笑:“悠闲一点,丢三落四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咦?”他满脸疑惑地看着萨妮娅,但刚刚的声音很显然不是她发出来的——对方继续上面的话题:“反正和平已经持续了不知道多久了,从今以后也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只是好好地享受每一天而已。”
“嗯——是啊——”海米尔宁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感觉有些什么不对。
“?”萨妮娅很明显地产生了疑问。
“你怎么了啊。”她靠近了过来,而海米尔宁内心当中的迷惑在一瞬间全部被她身上好闻的玫瑰花香所代替。他吸大了鼻孔,紧接着满脸通红地转过了头。
“你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吗,还是晒太阳晒过头了,没事吧?我找点水给你喝。”“喂萨妮娅。”海米尔宁用有些发抖的声音说道:“就是,那个。”
“嗯?”她声音温柔。
“能和我——”他回过头满脸通红地正打算开口,路旁忽然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当锵——!!”清脆回响着的金属音像是一声惊雷,让海米尔宁“咻——”地一声站了起来并且下意识地就把手伸向了自己的背后。
“你在做什么啊,海米尔宁。”“呃——”“喂!新来的,都跟你说好了东西要绑紧的啊,锅子摔坏了怎么办!”“对不起对不起!”路旁的货运马车响起了一阵责骂的声音。
那个声音再度响起,海米尔宁愣愣地维持着这个动作。看着萨妮娅那双纯净的蔚蓝色眼眸,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了吗?”恍惚之间,他仿佛从她的眼睛当中看到了雪景。
可这,明明是在秋季的帝国北部。
“真是,海米尔宁你胆子也太小了吧,这一点声音就被吓到了。”萨妮娅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再度打开了手上的书本。
“不是这样的......”他起初只是想要自我辩解,但说出这句话以后,却又感觉有些什么改变了。
“不是这样的......”他重新强调了一遍。
“不是,这样的。”然后在第三遍的时候声音变得沉稳了起来。
“她是生于狂风暴雨之中的花朵,即便风吹雨打也只是更加昂首挺胸地走下去。”少年垂下了头,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说出这样的话。萨妮娅的表情变得冰冷了起来,而原本生机勃勃的生个世界也都停滞了。
“我始终坚信着,不论面对怎样的命运,人类始终都能在那之后,跨过这一切继续生存下去。”
“她才不会甘心沉沦于这虚伪的安宁——”
“海米尔宁·安里孔,你怎么了?”她询问,声音已温柔不再,充斥着怀疑与警惕。而他垂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是一双伤痕累累,满是老茧的手。
那是满身疮痍的孤狼,独自摸索成长的人生当中留下的印记。
而不是在小镇,在众人的爱之中长大的少年那嫩白没有干过粗活的手。
“不。”他开口。
“我的名字是。”
“海米尔宁·海茵茨沃姆。”
“银卫骑士团团长,苏奥米尔元帅。”他挥手拨开了面前的迷雾,同时与她拉开了距离。
“结束这段幻境吧,萨妮娅。”声音从少年变成了青年:“这对你我而言都是一种侮辱。”
“.......”她沉默,但周围的环境确实地改变了。
“不,不是,是你有可能度过的,你期望度过的另一段人生。”许久之后她才开口,用平稳没有起伏的声音说道:“我有能力让它化为现实,海米尔宁。”
“你仍不懂吗?”
“那些不该死掉的人都会好好地活着,海米尔宁。不该经受的苦痛都会消失,你能过上你梦想中的美好日子。”
“你的手本就不应为了握剑而生,你太善良了,海米尔宁。即便是面对邪教徒你也无法确信他们就彻底是邪恶,你会因为对于自己正当性的怀疑而有所迟疑,你会想要找出真相,你会想要改变一切。”
“你总是试着改变一切,可这世界已经千疮百孔,为何不干脆推倒重来?”
“你真的......”
“不是她。”他咬着牙关,声音颤抖着,却拼命挣扎着向前。
“......我哪里不是了。”她的声音变得冰冷。
“萨妮娅......不会否定这一切。”
“不会逃避......”
“她不会沉溺于过去。”
“永远只看着将来。”
“是这个世界把我们塑造成这个样子,是啊,一切要是能够重来,所有的错误都被抹消,沉溺在美好的过去时光当中,该多好。”
“但现实已是如此。”
“她的温柔与坚强不是来自于无忧无虑的悠闲时光,而是在这漫天的战火当中坚强生长的。”
“她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是在狂风暴雨,在冰雪之中之中仍旧昂首向前的。”
“苏奥米尔的——”
“雪莲花!”
“萨妮娅是,不屈的。”
“所以。”他说:“你不是她。”
紧接着,握紧了克莱默尔的剑柄。
“咳呃——”因为冲击的缘故受损的内在使得海米尔宁刚站起来就感觉双脚一阵不稳,而他吐出了一口淤血,两眼发昏却仍旧借着大剑站了起来。
“现实再残酷也不会逃避,不会想要回到过去想要让一切的苦痛从一开始完全不存在。而是接受这些,跨越这些,带着它们通往明天。”
“若没有这一切的话,我也不会遇到这么多可敬可亲的人们。”
“可你们所爱的明天根本不存在!”愤怒的她一甩手臂:“嘭——!!!”一阵狂风袭来,海米尔宁插着大剑才勉强留在了原地。
天空当中一片深蓝,夜空中魔法的光辉和刀剑交击的声音还有同伴的怒吼在外面响起,这重新进入到了他的耳畔之中。
而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双眼闪烁着红光的她再度开口:“人类只会永远地重复着相同的错,因为贪婪,因为误会,因为恶意。即便是这场战争结束又如何?之后顶多数十年的短暂和平,一切还会继续。”
“一位暴君死去只是换来一个新的暴君,不平的事情在这里消失了在其它地方也还会重现。”
“既然如此让大家都获得了安详不就行了?为何你要阻挠我,为何你无法理解我?”她逐渐开始抓狂,溢出的黑色魔力在空气之中“噼里啪啦”地一阵闪烁。
“为何如此,骑士团长海米尔宁·海茵茨沃姆,为何你不接受这一切——!!”“嘭!!!!”魔法的光辉再度闪烁,在尘埃落定之后,摇摇欲坠的海米尔宁仍旧撑着克莱默尔站了起来。
“我不是......骑士海米尔宁,咳呃——”他再度咳出了一口血,用沙哑的声音说着。
“在你死掉的那天起,我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了。”
“现在的我啊。”
“只是一个愚蠢的男人。”
“你不可能明白的吧,守护这种东西,不单只是指物质上的。”
“我还要,将她。”
“将贤·者·萨·妮·娅·的·意·志,去守护。”
“去继承下来!!!!”高高抬起的克莱默尔直直朝着她的面部砍去,但在到达之前却被一阵冲击波给格开。海米尔宁被冲着退出了好几步远,地面摩擦出了两道痕迹,但他仍旧站着。
尽管浑身的伤口都在隐隐作痛,但他仍旧站着。
“那把剑.......是什么东西。”对面双眼通红的她显示出了戒备之意:“为何我差点没能挡住。”
“啊啊——”
“这个啊。”海米尔宁重新摆出了架势,这一次是剑尖朝下。
“这是一把。”头发落下遮住了他散发蓝光的双眼,而他用满是污垢破损流血的嘴唇。
说出了那个她赐予的名字。
“克莱默尔。”
紧接着。
一步向前。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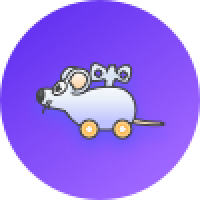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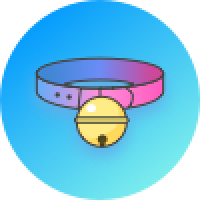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