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族人的选择并未出乎意料,他们与叛军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毕竟哪怕是意欲谋反对皇帝并无多少忠诚心的豪族,和人仍是和人。占据社会主体优势地位,打小就被教育灌输“我等生而高贵”思想的他们,是不可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些叛乱者与当权者之间的冲突,才进一步导致了少数民族等不受中央掌控的群体被“附带伤害”。所以要认真来说的话,这些人其实也和夷人如今面临的困难脱不了干系。
如此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令我们的洛安少女想起曾经的亚文内拉王国。
拉曼学者曾言“弱国无外交”,这一点换到民族上亦是如此。作为少数民族又不够团结的夷人,在和人开始内斗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就被卷入了其中。他们没有与任何一方平起平坐的实力,因此只能自认倒霉,逃亡,或是暂时依附其中一方谋求苟延残喘。
他们连置身事外这一个选项都没有,只能选则站队,或是灭亡。
自身并不拥有话语权的弱小存在就是如此可悲。这甚至不是针对他们进行的迫害,而只是因为其他人的反叛触及到了中央的逆鳞,导致他们加大了控制力度想要未雨绸缪预防更大规模的反叛而已。
甚至就连历史,都不会记载他们这些人。
因为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胜利者也许会讴歌对手以显示自己连这样的强敌都可战胜的强大,也许会对对手进行抹黑,但连站到棋盘上进行对决的资格都没有的小角色,是无人会铭记的。
每当时代的洪流发生了改变,总会有无数这样被卷入其中的小角色们被吞没,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激流之中。
而后人极少知道的也极少会在乎的。
是他们在消失之前曾做出过的。
犹如将死的星星一闪一闪,难以与皓月争辉,却仿佛在以最后的气力宣告自己曾用尽一切活过的。
那份挣扎。
“哗啦——”
3月伊始,新月洲北部大雨倾盆。
春雨冲刷着积攒了一冬的坚固冻土,让它们变得松动。但在那之前部分顽强的植物已经生根发芽从中钻出,在寒冷的初春之中尽可能地获取阳光,以领跑姿态占夺资源。
山上富有营养的土壤顺着雨水与融雪形成的小溪流到下方滋润了山谷与平原,结束了冬眠的动物们也开始出来觅食活动。
雌兽领着在冬日里出生仍不习惯于靠自己走路、踉踉跄跄的幼兽出来觅食,而饥肠辘辘的掠食者们则盯上了这其中较为虚弱较好得手的目标。
初春是生机勃勃的。
但如绚烂的花儿必然根植于充足的养分之上一般,这种生机也是建立在残酷的生存与死亡之上。
对野兽如此,对人类亦然。
“哗哗”落下的大雨拍打在鲜红的甲胄之上,“滴滴答答”地顺着头盔的弧度流下,又滴落在肩甲上,也掉落在光滑如镜的剑刃上。
“哈——”武士喘出的气息透过面甲的缝隙形成了一片白雾,他有意地把控着呼吸的幅度,避免一口气呼出的气息过多,导致白雾遮挡住自己的视线,给对面那个高大的异邦人得以击败自己的契机。
情况是不利的。
足有5名武士,16名足轻的己方队伍守着这个有掩体的关卡本应足矣。
哪怕在看到那些本该属于己方的夷人却与外来者狼狈为奸之时,他也未曾有多少畏惧——不过是些老弱妇孺组成的杂牌,又怎能与久经训练,每日都最少对着木人练上三时戳刺的职业士兵比拟?
他的内心是十分自信的,哪怕举起了反旗,也依然有作为和人贵族武士的自尊。
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佐以充沛的资金,饱读兵书,对最少三种以上的主武器了若指掌。
他自认不论面对哪一种情况,都已经拥有了合适的应对方案。手底下的人完全明白应当如何摆出阵型,应当以什么姿态迎击敌人,如何封锁,如何侧袭,或是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与其他任何武士家的儿子一样,他对兵书倒背如流,完全知道对方采取某一种进攻阵型的话,自己应当采取的是怎样的应对方法。
他做好了最充足的迎击姿态,随时准备变换阵型。
但对方。
没有采取兵书上所写的任何一种进攻阵型。
“欧伯!!”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这样喊着,紧接着那群夷人就乱糟糟地站在远方拉开了弓。
武士目瞪口呆。这些人手中的弓既没有相近的尺寸和拉力,甚至连所用弓矢的大小重量都有差异,射出来的箭雨歪歪斜斜,根本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打击。
‘这是何等愚蠢的杂牌军才会有的行径?’尽管这样想着,为了保险起见——因为夷人据说会在箭上淬毒,见血封喉——他还是让手下们升起了挡箭用的竹门,将对手的身姿与这波歪歪斜斜攻击力完全不足的箭雨一并抵挡在外。
临时以厚实楠竹配合麻绳制成的竹墙,加上滑轮与粗绳吊着同样材质的巨大门扉甚至足以挡住大弓的近距离射击。缺陷是没有屋顶,不仅无法避雨,亦难以抵挡头顶落下的攻击。
因此他们需要暂时下蹲,躲入竹墙倾角的下方。
这是万无一失的防御壁,他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所以按照最为标准的操作手法,避免不必要的人员折损。
他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对方还在几十米外,这墙壁也足有两米多高,只要等到箭雨过去,就可以开门迎战。
完全来得及的,按照兵书上的记载,这便是最为正确的做法。
他按部就班,在完成了抵挡之后令手下重新垂下竹门,然后在听到意外动静的一瞬间急忙地喊了一句“停下!”,却已经晚了一步。
“嘭!!”一只大手抓在了刚刚开始降下的竹门末端,紧接着用力地往下一压。
“哇!!”粗大的麻绳被以极高的速度往前抽去,使得未作准备的那名拉门足轻双手都被划得血肉模糊。
‘该怎么做?’在这一瞬间,武士惊觉自己脑海中冒出来的竟是这个想法。他立刻拿出了专业素养把这个念头驱逐出脑海,但下令却也已经慢了一拍——正如所有照本宣科缺乏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一样——他不懂得如何应对那些在兵书上没有教他应对的情形。
他缺乏面对实战环境当中复杂多变的情形,所应有的反应能力。
饱读兵书诚然重要,但光会对号入座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内容应用到实际战斗之中,总结出来自己的规矩。
他光是读了书,还没有“读破”书。
武士在极短的时间内意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他的内心当中一瞬间经历了自我反省以及重新打起精神的全过程。
他是无愧于月之国四千年文明的精锐武侍阶级。
可他遇到了亨利。
“嘭——!”被当先一脚踹翻的足轻摔倒的过程当中贤者“咔——”地一声接过了他手里的长枪,紧接着转过身的同时旋转了长枪枪尖朝下就戳中了另一个人穿着草鞋的右脚。
“哇啊啊啊!”这名足轻惨叫着下蹲的一瞬间贤者按着他的后背整个人翻了过去闪过了其它两人的攻击,紧接着一把扯下了足轻头顶上铁制的斗笠头盔,当做飞镖丢中了远处正打算拉开大弓的一名武士。
“锵——当——!!”单手挥舞的克莱默尔轻松地击断了对手试图拦截的长刀紧接着劈开了他的脖子,紧接着面见鲜血亨利也丝毫没有半分波动欺身向前抓着这人的身体背对着竹墙以他肉身做盾拦下了3枚箭矢。
他并不拘泥于用克莱默尔战斗,哪怕这确凿无疑是他手中最为强悍的武器。
对手身上的刀,对手的长矛,盾牌,都手到擒来。甚至自己的肘关节,用脚踹,拳击,运用关节技。
月之国的武士们都最少能够熟练使用长刀、长枪和大弓这三种武器。他们对此引以为豪,但这种自信在这个男人展现出来的东西面前碎成了一地。
“咔——锵——”刀与剑相交,武士正打算将刀往后抽去再劈一刀,亨利却已经变换了克莱默尔的角度顺势往前捅了出去。
“咳呃——”喉咙被捅穿的武士一瞬间咳出了血,他仍强撑打算继续作战,但贤者手腕一翻剑尖一扭扩大了伤口就抽出了大剑。
更高的身高带来更长的臂长,佐以一米五长度的克莱默尔大剑。
“勿要近身,唯有以长枪或大弓克之!”红武士大声地喊着,但杀红了眼的其他人却也已经听不进去。
他们一个个冲上去,然后被干净利落地干倒。
高大的异邦人以与那身形完全难以匹配的灵活性闪避或是以死去武士的尸身作盾,令他们所有的攻击连一根毫毛都没能伤到。
21个人,转眼之间只剩下拉开距离的红甲武士一人。
淅沥沥的春雨忽然下了起来,并未披上避雨蓑衣的武士,很快就浑身湿透。
冷气侵蚀着他的身体,使得握刀的手指都有些僵硬而麻木。
视线因为湿气而暂时模糊了起来,甲胄下方穿着作缓冲的铠下着也因为吸了水开始变重。而待到水汽沉寂,站在对面的异邦人垂着手里那柄剑被雨水洗净了上面受害者的鲜血,显露出,那闪亮如新的表面纹理。
武士看到了上面黯淡的花纹。
那像极了新月洲大地的高山与流水——这不是异邦之物,哪怕外形千变万化,他都仍旧能够一眼认出。
“投降吧。”从面容区分甚大的异邦人嘴里吐出的本国语言,却并不显得生硬。
“士可杀,不可辱。”武士回应着,控制着自己缓缓地呼出了气。
错误没机会补正了,实战经验,恐怕也已再无积累的可能性。
他不是固步自封的愚昧之徒,不论是学识、头脑还是武艺都是一流的,缺乏的仅有经验。若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也许会成为月之国的一代名将。
但这样的结局也不坏吧。
“对武人而言,能跟拿着这种剑的对手交手的话。”
“此生已无憾。”“踏!!”着鲜红甲胄的左腿狠狠踏下,他高举着尺寸不输克莱默尔的长刀,以月之国武侍常有的冲步高速拉近距离,紧接着用比里加尔剑客更快的速度挥下了手中的武器。
“当!!”与克莱默尔碰撞在一起的长刀分毫不让,就连亨利也之微微皱起了眉头,他注意到了这把刀的不同之处,它并没有像是其它那些武器一样直接就折断或是卷刃。
“拿命来!!”红武士大声地咆哮着“锵当——!”一声擦着剑刃朝着亨利的下巴刺去,而贤者的反应则是抬起克莱默尔用护手卡着刀刃把它整个往上抬接着往外挪去,但对方也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立刻往后抽刀“嚓嚓嚓——”火花四溅,而武士收回武器之后往后退了一步紧接着将它高高举起。
贤者改成了双手握剑,并且垂下了剑尖,是他惯用的起手式。
“拿命来!!”武士红色的面甲绳索崩落,露出一张年青的,但充满了怒容,双眼之中燃烧着熊熊热情的脸庞。
“哈——”亨利呼出了一口气,是呼吸。
亦是叹息。
长刀落下,大剑上撩。
“咻——!!!”“当!!!”
“咻咻咻咻——”
“夺——”
折断的刀尖,插在了软化的泥地里。
雨淅沥沥的下。
尽管硬度不相上下,但它却缺乏克莱默尔举世无双的韧性。
短短几次交锋累积的暗伤最终变成了裂痕,使得这把也算得名贵兵器的长刀就这样折损。
“咳——”被从高举双手姿态露出的腋下甲胄缝隙捅进心肺的武士,除了咳嗽已经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嚓——”贤者拔出了克莱默尔,然后随手甩干了血迹。
“咚——”红武士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
“.......”姗姗来迟的其余一干人等站在竹墙的门口,看着一地鲜红的死尸,与站在冷冽春雨中,一脸平静地单手握着克莱默尔的贤者。
“阿拉咖密.......”曾被冠于某头棕熊身上的名讳,藉由夷族人领队之子的嘴,被带着几分尊敬,几分畏惧地,安置在了这个黑发男人的身上。
“接、接下来。”沉默了许久的夷人领队终于干巴巴地开口说道,稍微熟络起来之后,亨利等人知晓他并不只是不熟悉和人的语言,还稍微有些结巴:“我们应该,朝、朝着东南方向走。那里水路通畅,临近沼泽。虽然有很大的和人村庄,但人员来来往往,打扮一下,没有人会投来过多注意。”
“唯、唯一有问题的,只有你们带的,这、这头灵兽。”领队男人回头瞄了一眼小独角兽:“这、这个体格,很难假扮成驴子,马、马又是和人武士专用——”他话没说完,就看见亨利指了指地上的那些死者。
“啊——”不少人都发出恍然大悟的声音,连连点头。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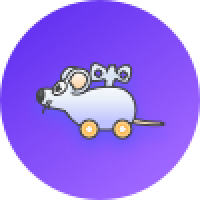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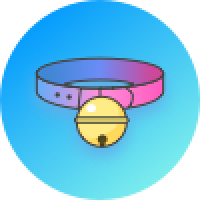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