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依旧嘈杂,我像往常一样路过此地,从南边向着北走,这是我回家的路。沿路商贾云集,他们左手揣着珠宝串子,右手抚摸柜上钱财,身穿细棉毛衫,脚覆深青云靴,满脸横肉,笑声似要吃人!我不敢多停留,和大多数百姓一样低着头快步走过。
我从城南商区回家约莫要走半个时辰,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脱鞋,毕竟有十里长路,那粗糙的草鞋又怎能这么折腾。家徒四壁下,即使是一双草鞋想要更换也是难上加难。
家中未见二老,我有些惊疑,故作镇定地认为他们应该是去集市淘剩菜了。往常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会他们回来时脸上挂着笑容,双手拿着淘来的剩菜,嘴上还止不住地嘟哝着这些菜够咱们吃好多天了。
显然今天并不同于往日,我坐在草垫上看着那扇被风吹得嘎吱响的破木门,看着阳光逐渐暗淡,看着白变成黑,心彻底沉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去哪了,也没法知道。
那是我最难忘的几天,明明是刚记事的年纪,可对那一切至今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几日天气阴沉却无风无雨,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我就那样在家中坐了两天,一直盯着木门,余光瞟到了许多商队的走狗到村中拉壮丁,其实我此时心中已有了定论,可我仍抱有希望,我不想他们出事,即使我当时什么都不懂,这是本能。
第三天,有商队的人往家中丢了一小袋铜钱,我拖着虚弱的身子追上去问那人我爹娘去哪了,那人长得很高,低头看我骨瘦如柴,可能实在是于心不忍,又往我这丢了一袋铜钱,但我太虚弱没法接住,只能任那袋钱砸在我身上,随后掉在了地上。
“他们死了。”
仅有四字,仅有四字,这是我构思过了无数次的结果,演绎了无数次的结果,但我还是接受不了,到现在也还是接受不了,我崩溃了。
我抱头痛哭,声嘶力竭地喊着爹娘,脸深埋在了泥土里。那发钱的叹了声气,转身走了。走前来了个他的弟兄,满脸凶相,那弟兄走到我面前看了眼屋子内,发现屋内地上有一袋铜钱,于是把那袋掉在地上的铜钱捡走,向着前头那高个说道:“为何给他发两袋钱?”
高个回道:“看他可怜。”
“可怜他?非亲非故不说,若是被上头发现你这样私自发钱,你我都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知道,可……”
“打住打住,这事莫要再提,只是些下人罢了,无需怜悯。”凶相男脸上凶相更甚!走前仍在抱怨,“这土皮村还真是村如其名呀,穷得只剩土了,这地踩着都脏我脚!要不是赵公子要求…….”
我哽咽间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吃力地想抬起头看一眼那给我发钱之人,事与愿违,泥土混着泪水黏在了眼睛上,我只能依稀看见他所穿衣物背上绣着一大一小的小球,小球挡住了一部分大球,我深深地记了下来。
本是无风无雨之日,他们走后却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泥路坑洼泥水交错,我就这样浸在了泥水中,忆起往昔,企图坠入梦境,回到过去。
等我醒来已是翌日清晨,积水经过一夜沉淀显得颇为清澈,我脸上则是被风干的泥尘覆盖。难得休息一夜让我稍微恢复了些体力,我用水坑中还算清澈的水洗了把脸,看着水中我面庞的倒影,又忆起了昨日之事,顿感无助,我担忧未来,不知所措。
我带着那袋钱落魄地走在街上,向南走,向那青潭镇走去。
迎面奔来一辆马车,轿厢镶着金边,定是大户人家。明明街道特别宽敞,左右两边也没并无遮挡,可他还是向我冲来,没有减速,没有转弯,车夫面爆青筋,吼道:“哪来的乞丐,站在路上碍眼,碾死吧,哈哈哈哈!”
车厢内那人应道:“随你。”语气轻佻。
太可悲了,我那时觉得这一切都没有道理,宛如梦境,为什么他们衣着华贵不说还能毫无顾忌地打压百姓,为什么所谓的公正形同虚设。这是人恶,是风邪。
我竭力向路边跃去,马车实在太快,我还是被马车的气浪冲飞了出去,险些摔断双腿。
“哟,躲得挺快,”车夫见没撞到我回头看来,“算你命大,滚吧,哈哈哈哈哈!”
恶心的笑容,和那个大腹便便的商贾一样令人作呕。
我站起身子,压抑着满腔怒火,却无处可发。如此渺小,被人视为草芥。如今豺狼当道,百姓苟活于世,一切都显得暗无天日。
此代不争,此后世代仍是如此,如此苟活,倒不如舍命抗争。与时代之厮杀必将鲜血淋漓,但社会之变革配得上这淋漓鲜血!
天地不仁刍狗走,无私大公尽被欺;奈何桥旁撑英豪,誓与尔等同俱灭!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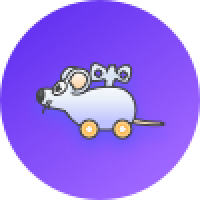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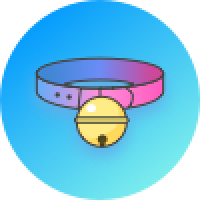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