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摸着,师父为了将我的身子还原,一定又跑去巫蜀的巫山采药了,也一定为了炼药消耗了许多法力。
“师父——!”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流出,抚过还未完全愈合的脸颊,融入绽开的血肉中,师父说,那是他身上的两块肉,长出来的血肉。
师父醒来,伸了个懒腰,然后起身,挥一挥衣袖,身上化了件雪白色的新衣,依然是他喜欢的那种简约风,除了白还是白,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师父缓缓向我行来,我不知为何,竟有些害怕,身子颤抖着。
师父走到药缸旁,却没一丝责罚的意思,柔声细语道:“这水,该凉了吧?”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没有笑容却不冷着一张脸的师父,心里暖暖的。
一般师父的脸上,除了郁闷之时皱得一字眉九曲十八弯外,便只走两个极端,一个笑得灿烂如个永远长不大的孺子,一个高冷似一块千年的寒冰。
我从未见过这样温柔的师父,生怕说水冷了,他便会又耗费法力给我温水,而那样的话,师父会更憔悴。于是我忍着冷撩着药缸里的水在身上洗澡,边洗边笑容满面道:“师父,水温刚好。”
师父一脸郁闷,微微挠头,许是觉得水温不该刚好才对,又不知说什么,我装傻道:“师父,水很暖和,您老人家,要不要一起洗啊?”
师父两颊如被火烤,一下烧得通红,我趁胜追击,“师父,您再不进来,一会水可凉了。”
师父转过去,背对着我:“为师……为师还有些事未处理,药水宝贵,若还温和,你便记得,一定要多泡一会。只有多泡一会,让药入了皮肉,效果才更佳。”说完,不待我回答,便径直走了出去。
师父走后,我冷得直打哆嗦,却不想辜负师父的一番心意,便咬牙继续泡着,不一会鼻涕直流,寒颤一个完了接着一个,依然坚持着,心想:师父一定在门外守着我呢,若现在出去了,便辜负了师父的一番苦心了。
事实上,我的确辜负了师父的一番苦心。
以师父的法力,怎会不知药缸中的水冷?
师父怕我的身子被冷坏了,便故意说让我多泡一会,本想着,以我常与他作对的习性,断不会多泡一会,怎料这一****终于长大了,不再与他作对。
直到天色暗沉之时,我都没离开过药缸,哆嗦着鼓着眼,心中不停暗道:“师父采药辛苦,我不能辜负!不能辜负!”
这一次的执念,我染了伤寒不说,本见好转的伤口,在冷药水中又一次泡开,药水渗入了肉中,痛得惨叫不止,却又咬着牙继续泡,“多泡一会,只要再多一会,师父的一番辛劳,便值得了。”
这时我听见师父喊着我的名字,我想答应,却又怕自己忍不了痛乱叫被师父看不起,便一只咬牙忍痛泡着不开口。
不一会,师父便找了过来。
师父进门便见着咬牙泡在药缸中的我,惊讶得“啊!”了一声。我望着师父愁眉不展的样子,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又做错了,竟然“呜呜呜!”哭了起来。
师父被我这一声哭弄得火急火急的,全然不顾我们的身子男女有别,一瞬闪到我跟前,俯身下来,将我赤裸裸的身子整个从药缸中抱出,然后抱着我转身,一步步走到床边,轻轻将我我放在床上。
我傻傻的望着师父,师父皱着眉,眼角挂着泪,细长白皙的大手伸向了我的身子,我潜意识里蜷缩了一下,师父的大手顿在半空中,师父含泪说,“一定很疼吧?”
我微微颔首,师父凝神运气,细长白皙的大手撑成一个大掌,掌心对着我的身子,我感觉到一股暖流向我袭来。
师父的大手缓缓移动着,凌空抚着我身上每一寸腐肉,一寸寸腐肉奇迹般一点点愈合,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师父在消耗修为替我疗伤。
我想起身阻止师父,却发现身子被师父的法力禁锢了,动弹不得,望着脸色越来越惨白的师父,泪如泉水般自心底涌出,我哭着大喊:“师父!不要!不要!”
师父皱着眉,惨白的脸色变得泛黄,又渐渐染上了一层绿,额头的青筋更一条条绽出,形容痛苦不堪。
我不停地叫着,可师父毫不理会,依然源源不断地向我的身体输送修为。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心上好似刺了把剑,剑身来回抽搐着,心上的血缓缓流出,痛不欲生。
哭喊着,我不停的哭喊着,“师父!快停手!师父,徒儿求求你了,快停手!”,可师父的眼神无比的坚定,好似头怎么也拉不回的牛,依然毫不理会我。
顷刻,我感觉体内充满了法力,便试着运气,谁知那股法力完全不受控制,我疯了般“啊!”一声大吼,几道白光快如闪电从体内飞出,师父一瞬飞了出去。
我紧跟着飞了出去,却没及时接到师父,师父重重摔到地上,“啊!”了一声,又“咳咳!”两声,嘴角吐出半大口鲜血,我大叫着“师父——!”上前扶他,师父却一掌击中的额头,我晕了过去。
我醒来之时,师父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块白布,布上墨迹未干,赫然写着,“为师有事回南海一趟,小白脸晚点便过来。”
我看着那张白布,心隐隐作痛,这时屋外刮起了风,窗柩“咯吱”作响,我盾声而去,只见一个白影闪过,我大叫着“师父——!”跟了上去,一瞬便追到了天道院前院。
我又冲着那白影大叫了声“师父——!”白影闻言,停了下来,却一动不动,我又大叫一声“师父——!”,白影动了动,一瞬化作股青烟,消散在门下。
我一跃而起,心中暗暗捏诀化作股青烟,向着白影的方向跟前,却“咚!”一声落地。
我犹如撞到了一面墙上被弹了回来般,重重摔倒在地。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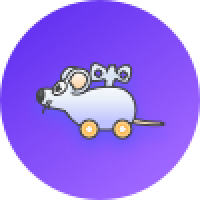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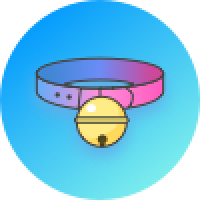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