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兄!”突然听到子渊这声叫唤,回神过来,尔后是一袭紫衫入眼,子渊不知何时又扑了上去,他将师父抱得更紧些,想托起爬到地上的师父,却被眼神恐怖的师父反手大袖一挥,抛出数丈。
我急得赶紧搀扶,口中连连“师父!师父!”的哭叫着,我紧紧抱着师父,想试着探出师父到底中了什么毒,师父却疯了似的,形容抽搐着,眼睛一瞬变得血红,我吓得哭得更猛,不停地“师父!师父!”的叫着,师父却又一挥袖,我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周围的空气极速的流动起来。
师父这一挥袖,不知有意无意,竟将我抛出结界之外。
结界之外,不是素日里天道观门前热闹的大街,而是幻境中的天道观前院。
飞出来时,我正巧撞到了前院中那方大鼎的侧面,“啊!”地惨叫一声,便重重摔在地上。
我忍痛想站起来,却痛得无法动弹,抬眼摄入眼瞳的,是许多双诧异的目光死死望着我,望着不知从哪突然飞出来,又“咚!”一声撞到大鼎之时“啊!”一声惨叫落地的我。
我试着又抬了下头,却感觉脖子似断了般,心急如焚,哪有时间理会这些眼光?
于是我聚气凝神,观微神魂出窍到自个的身体里走了一遭,吓得神魂大叫:“师父!你好狠的心!”
我整个身子里的三百多根骨头,大多断了不说,有些还摔得粉粹。
若不是修炼的日子长了些,只怕师父这一挥袖,我得去西天见佛祖了,即便见不了佛祖,必然也会下地狱一番,然后过奈何桥,喝孟婆汤入轮回——呃……突然想起,师父说,我是一株檀香,一株不死不灭的万年檀香,即便某一日死了,也去不了西天,更入不了轮回。
师父曾告诉我,我是个不死的奇葩。在这个世间,万物死了,都能入了轮回,而我不但不会死(师父说,其实是目前没有死法),即便有一日有了一种死法,真的死了,灵魂也入不了轮回,只会如空气般消散。
我问师父,为什么我死不了,师父望着我,眼神恍惚,好像想起了什么,又没说什么,只叹息道:“哎!妖姬,许多事情,终有一日,你会明白的。”
师父,你好狠的心!即便你知我是个死不了的奇葩,但这断骨碎骨之痛,我一个十几岁大的小姑娘,又怎受得了?
我含着泪,望着身体里那些断裂的骨头,不由得想,如今我外面那副身子,着实该痛不欲生吧!
事实是,只是一个神魂的我,已痛不欲生,不过这种痛不欲生,并不是身子,而是神魂的痛不欲生:师父从未这样,对我狠心过!
神魂化作个小人,跳到我的脖子上,扳起几个颈椎骨扭了扭,“磕!”“咔!”几声,错位的脖子接上了,又一跃跳到腰上扳几根肋骨,又“咔擦!”,腰上肋骨接上了,我的神魂就这样在整个身体的骨架中徘徊,不一会,整个身子里未碎掉几十根大骨头,一一被接上。
小人站在肩头骨上,仔细扫视全身的每一块骨头,确定断掉的骨头每一块都接好之后,我长长的舒了口气,尔后一跃而起,回到入定身体的刹那——痛、断骨碎骨之痛,一一袭来,我惨叫着,叫声十分吓人。
天道院内那些诧异目光的主人,许是被我这声惨叫吓到,纷纷转身就往天道院外跑,有的边跑边叫着,“妖怪!、妖怪!”
我试着凝神运气,让修为遍布身体每一块接好的骨头,这些骨头在修为的滋养之下,长出了一块又一快小骨头,如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长出桠枝一样,却快得只在一眨眼。
这一眨眼的工夫,逃窜的人群并没跑多远,我望着他们,心中大为不解,“不过来了个陌生人惨叫几声,至于吓成这样?”
但我转念又想,师父曾说,人类是群居动物,群体意识过强,我们若往往吓住了几个,一群人便不看什么,跟着那几个被吓到的逃窜。
“哎!这人啊……真特么胆小!”
但不过顷刻,我便自我否定了这声嘲笑。
是一滴凌空而来的血,让我做出这个自我否定的。墨色粘稠与我身体里一脉相承的血。
我不由得抬起头,只见虚空中飘着个血淋淋的躯体。这些人很显然,并不是被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天外飞仙”吓到的,而是被这副血淋淋的躯体吓到的。
这幅躯体,除了我狠心的师父,还能有谁?
但师父适才,不是中毒了吗?怎么……难道师父的毒,解了?
师父穿梭在虚空中,地上的人们你追我赶,叫声不断,师父衣袂飘飘,大袖一挥,院中平地刮起道大风,天道观的大门“吱吱!”两声后,“砰!”一声关上,向外逃窜的人们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却依旧冲着紧闭的大门跑,师父凌空一个侧翻,稳稳地落在了地上,衣袂飘然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人们见状,纷纷叩首求饶,整个天道观内,顿时只听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哪!”的哀求。
师父拂袖,抹了抹嘴角的血迹,想说什么,却又没说,远远地望着我,眸中好像蕴着泪,眼神在对我说,“还痛吗?”
我不由得大叫了声“师父——!”,纵身跃起,凌空踏虚而去,落到师父边上。
“哼!”
这一声冷笑,听着短,却萦绕于心,摄魂震魄,我一个修行之人,尚且这般感受,更别说院中的众人了。
他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尔后四肢开始不停抖动,渐渐蜷缩起地上,似疯了般颤抖着,眼神呆滞极了,仿若看到了魔鬼。
望着这一幕,我心生怜悯,却无可奈何,只能看了一旁的师父一眼。
师父面无表情,仿若一座冰山,丝毫没救人的意思。我扯了扯师父的衣袂,师父扭头看我,眼神冷酷无情,“你是想说,让为师救救他们,对吧?”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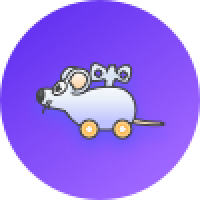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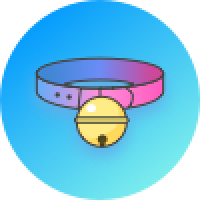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