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瞻看着高台之上言笑晏晏的王莘,心下叹惋,这样好的女郎,怎么命运这样凄惨,早早的成了寡妇,真是好人没好报。
王莘还不知道自己被新晋的将军可怜了,只顾着和褚方云讨论着衡阳王萧策人皮之下到底是一副怎样的心肠。
酒过三巡,王莘略微有些醉意,褚方云提议两人出去吹吹风,散散酒气,也顺便看看这建章宫这些年是否有什么变化。
刚出后殿侧门,冷风拂面,王莘瞬间清醒不少,心下的盘算也不断清晰。
从前,她对萧策几乎毫无印象。今日一见,确实符合一切她对佞臣的想象。
看似放纵不羁,实则处处拿捏分寸。行礼问安之间,抓不住他任何错漏。就连放肆,也不会讨人厌。
这样一个对手,实在难对付的紧。
杳玄无论如何筹谋,所图不过一个权字。
可萧策行事诡异,虚实难测,寻常人根本猜不透他的意图。
听说,从前常常有人同他争论,只是在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扰乱下,很快那人就被绕了进去,忘记自己来寻他的意图。
虽然除夕宫宴,两位皇后今日穿的仍是素净,出了大殿也没带几个侍从,来往的宫人也颇有轻视之意。
连路过问安也是敷衍而过,褚方云叹道,“当年的宫人已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如今哪里还指望她们识得我们。”
曾经前呼后拥,出行仪仗那样声势浩大的褚皇后,到现在黄门侍婢女对面不识,落差之大,可以想见。
王莘拍了拍褚方云的手道,“你到底还享受过”,顺势委屈撇了撇嘴。
褚方云一愣,低声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好比的。
两人说笑间越走越远,仿佛快到御花园了。
只是,这冰天雪地的,两人却瞧着远处御花园姹紫嫣红一片,心下大异,走近了前去看,才发现,白雪皑皑之上,是用各色丝绸、素绢编织成的花朵,远远看过去实难分辨。
就连太液池旁垂柳也用青色丝绦包裹,凛冬之中,却是一片春色满园。
两人被震惊到失声,纵使褚方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也从未如此奢侈过。
那些丝绸都是汴州进攻,匠人们数日才能织就绣成一寸,就被这样裁碎用来铺在雪上,铺在干枯的枝丫上。
这实在是,暴殄天物。
过了许久褚方云才开口,“这,萧霁竟如此靡费么?!”
王莘道,“今日宫宴靡费之数不下万金,以萧霁实力来看,不像是他的手笔。”
萧霁出身旁支,却远的不能再远,虽然也是皇亲国戚,确实穷的叮当响。
就算登上帝位,那宫中私库也就是个摆设,哪有什么钱财。
“两位嫂嫂不必忧心,这些都是微臣当年在杳玄私库收缴的,如果能博得两位嫂嫂的一笑,便是这些压箱底的死物的福气。”
王莘,褚方云皆是一惊,回头去寻声音出处,却发现今夜她们讨论的主题衡阳王赫然在她们身后,正好整以暇的盯着她们。
侵略性的眼光在两人之间扫过,便顿在王莘身上。
双方见了礼,褚方云艰涩开口,“就算是收缴而来,也不应如此浪费才是啊。”
就算她不打听,她也知道前线吃紧,打仗没钱怎么行呢。
萧策见褚方云发问,这才把视线挪开,扯了扯嘴角道,“这些布匹丝绸搜罗来的时候,成匹成匹的都已经腐烂,才让匠人裁了仅存的还未发霉的布料,才成就这般胜景。”
倒是心思精巧?褚方云见自己误会,开口致歉,萧策摆了摆手道是无妨。
萧策肌肤胜雪,倒是比寻常女子还白净些,眼窝深邃,鼻梁高耸,瞳孔透着幽幽的光彩,依稀能看出当年昙花一现的那位胡人宠妃的绝世风华。一绺鬓发飘在额前,想来是与人劝酒时从松散的发髻之中脱出,此时的萧策周身阴郁之气沉下,倒多了几分风流贵公子的味道。
只是,她们可不敢把眼前这个人和寻常人家的风流公子联系在一起。
也不知何时这人跟了上来,两人皆是一阵不自在,可见不能背后说人长短,最好回去了悄悄说。眼见着冷场,两人便要告辞。
王莘转身离开时,萧策却突然出声,仿佛从牙缝中挤出前两个字,“哀后,这花好看吗?”
王莘惊异回头,萧策是在叫她吗?
看着萧策确定的眼神,她点了点头道,“美虽美,到底靡费。”
对于发霉的丝绸和布匹,自有一套处理的办法,先用清水洗涤,再覆以烈酒,霉斑便能去个七八成。晾干以后,绣上花鸟鱼虫遮盖,便能低价售出。
且这样耗费巨大用作景观,明朝之后被建康中的豪门知晓,不出一日,便能群起争相效仿,这便不再是几十匹霉坏的布料的事了。
各路世家的后院,怕是都要在这冬日都变成阳春三月,绿意盎然了。
他们也自然不会用什么发霉的布料,他们用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上等丝绸。
萧策只在心中喃喃,若是喜欢,这点靡费算什么。
这些年,有不少人为他操心婚姻大事,可他就是忘不掉那句掷地有声的,“我王莘要嫁便嫁这天地间最好的儿郎!”
就像他对濒死的父皇说,他要做就做这南景说一不二的掌权者!
那时父皇已经病入膏肓,神志不清,也不知道将他这个落魄皇子遗忘到哪个犄角旮旯里。他趁着太子萧豫不在,悄悄潜入寝殿,对着回光返照的父皇,一字一句发泄着这些年的怨气。
明明他也很努力,为什么父皇就是不肯施舍一个眼神?
只是,躺在榻上的虚弱老人只看着他一言不发,等他赤红的眼底戾气散去才嘶哑开口,“那又如何?”
原来在他的父皇眼中,无论是他的怨气还是他的努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萧策失控冲向病榻上的人压抑吼道,“到底是为什么?!就因为我的母亲是胡人?可既然是你们要生下我,为什么又弃我于不顾?”
他的母亲生下他之后,没几年就郁郁而终,就这样在南景后宫中短暂的绽放和凋败。
他的父亲对别的兄弟都能一视同仁,偏偏对他疾言厉色,就因为母亲卑贱的出身?可当年再卑贱,也曾宠冠后宫,一朝失势,就要被丢在角落里自生自灭,任人欺凌吗?
只不过,他的父皇被这样一吼,精神急转直下又陷入了混沌之中,萧策冷冷丢下一句,“既然你们踩我入泥土,那我便要做这南景说一不二的掌权者。”
眼见着走远了,褚方云才问王莘道,“你们从前认识?”
王莘摇了摇头,她在脑海中搜罗许久,也没记得和衡阳王有什么交集啊。
褚方云面色纠结道,“阿姒,若有一日,阿豫落败,跌到绝境,你能不能答应我,救他一命。”
她已经放弃了萧豫,但对于曾经夫君的那些情谊,她还是忍不住心软。
只是王莘却想,当年,若是他有为褚方云思考过一分一毫,就不会宫变时一个人死遁了。他的贴身黄门尚且能保全,就连自己的妻子都能蒙在鼓里。他难道不知道留下褚方云一个人面对那群刽子手,可能的结局和下场会如何呢?
褚方云幸运一次,却不会一直幸运。
她是同情萧豫的遭遇,好好的皇帝做着被拉了下马,又险些丢了命。
只是他既然投了杳玄,做了杳玄的傀儡,便注定是她王莘的敌人。
她深谙一点,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己的残忍。
褚方云以为萧豫无辜,既已身在局中,便都是棋盘上的棋子。既入赌局,便无一人无辜,也不能以常理辩是非对错。这场赌局,只论输赢。
这权势场的赌局,赢则青史留名,败则遗臭万年。
褚方云有此一问,应当是觉得萧豫会输?
王莘还未作答,褚方云就苦笑道,“从前我见萧策次数也不多,不了解此人。可我了解阿豫,与萧策相比,阿豫斗不过的。”
手段不够狠,心肠不够硬,都是当权者大忌,而也都是萧豫的特质。
王莘默默良久,下车时才对着褚方云点了点头。
王莘一夜辗转反侧,只觉此行唯一的收获便是,萧霁和萧策之间应当不是表面那般和谐,那么就有争取萧霁的机会。
只是,翌日,顶着两个黑眼圈的王莘和褚方云就被北宫门口堆满的礼物再次震惊到失声。
哪有人这样送礼的?明目张胆且...肆无忌惮。
褚方云揶揄看向王莘,这是什么情况?
王莘也是一脸惊异,她不记得她和现如今的骠骑将军刘子瞻有什么交集啊?
褚方云悄悄耳语道,“昨日是衡阳王,今日是骠骑将军,你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
王莘一把拍开褚方云的手,微瞪了她一眼,真是人与人之间距离产生美,从前也不见褚方云这般促狭。
王莘立刻派人探听这是什么情况,只听王府今日清晨也收到类似的大礼。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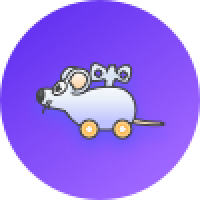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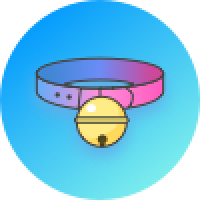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