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娘娘面露失望之色,她拍了拍扶手,叹道:“好了,不要再说了,你们还年轻,往后有的是机会。”她话锋一转,又对上了我,“至于承王妃,你已嫁作人妇,往后不可再这般胡闹,既然王爷对你青眼有加,你便应当服侍好王爷,早些为皇室开枝散叶、诞下子嗣才是。”
“还不赶快谢恩!”李世承凑近我耳边小声提醒着。
我整个人都处于懵圈状态,李世承扯了我一把,我才和他一块儿跪在了地上。
我学着李世承的样子,对着太后娘娘行了个跪拜礼:“儿臣(臣妾)多谢母后体恤。”
太后娘娘笑道:“乖了,都起来吧。”
我和李世承又坐了下来,刚落座就听皇上说话了:“母后,初儿作为皇长子,既已大婚,不如择吉日将老五、老六、老八的婚事也一并办了吧。”
太后娘娘点了点头,又说:“长安这丫头的年纪也不小了,也是时候给她找个婆家了。”
“皇祖母,长安才不要嫁人,长安要一辈子陪在皇祖母身边。”长安公主揉搓着衣角,羞得满脸通红。
“若是将你许配给安国侯世子叶君逢呢?”皇上问,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
长安公主的脸更红了,她揉搓着衣角,忸忸怩怩道:“儿臣全听父皇安排。”
太后娘娘连声应道:“好好好,哀家也觉着两个孩子很是般配。”
“回皇兄,臣弟觉得此事甚为不妥。”李世承蹙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皇上一脸疑惑:“哦?此话怎讲?”
李世承拧眉认真道:“安国侯府三代单传,他们叶家独苗一根,将来肯定会纳上几房妾室,到时还不委屈了咱们长安?”
太后蹙眉:“这倒是,咱们永朝的驸马向来不许纳妾,他们叶家又三代独苗,委屈了两边都不好。”
我这才想到,叶君逢是太后娘娘的外孙,她再疼长安公主,也不会委屈了自己的外孙。
皇上不动声色地问道:“八弟可有合适的人选?”
“兵部尚书杜正霖之子杜月怀。”李世承答道。
“嗯,此事日后再议,容朕好好考虑考虑。”皇上笑道。
又是一阵闲谈过后,众人辞别太后娘娘各自散去,我也跟着李世承往殿外走,他没个好脸子给我,狂甩着衣袖,大步朝殿外走去。
他似乎很是心烦,理都不想理我,脚下生风,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我在皇宫里转来转去,最终也没能找到李世承,这家伙不会撇下我,自个儿回承王府了吧?
这么想着,我心里就更气了,至于么?为了一个女人,将我晾在这里,至于么?
我又不是容不下其他女人,母后同我讲过,她说,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喜新厌旧是他们的通病,只要牢牢抓住正妻之位,管他怎么闹腾。
父王不就这样么,后宫宠妃一大堆,不也没亏待了母后不是?
我嘴里咒骂着李世承,将脚下的石子踢的七零八落,真没见过这么讨厌的人!
“嗬,这不是皇婶么?”一个嘲弄的声音突然响起,不用看也知道是李元齐,试想一下,谁能有他这么无聊呢?
我故意将头埋的很低,狠劲踢着脚下的石子,像是发泄一般,心里咕哝着:去你的李世承,去你的李元齐,都是些讨厌的家伙,看我不把你们踢碎!
“皇婶,还记得我么?”一个好听的声音钻入了我的耳朵里,听起来很是陌生。
我抬起头才发现,有五个少年正缓步向我走来,李元九与李元齐自是不用说了,我本来就认识,提到李元九,我不免多看了他几眼,呃,他还真是瘦了呢!
再看其他三人,五皇子、六皇子、八皇子,嗬,这是都到齐了呀!
“皇婶,还记得我么?刚刚皇叔介绍过的。”好听的声音再次响起,出自其中一个少年,呃,他是哪个皇子来着?五皇子?六皇子?八皇子?管他呢!
“理她干嘛,五哥,咱们走,你刚回汉京城,咱们哥几个今晚还要给你接风。”李元齐白了我一眼,语气里满是厌恶。
呃,原来他是五皇子,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皇叔呢?”五皇子又问,目光更是肆无忌惮地落在了我的手腕处。
他的目光太过锐利,看的我直发慌,不知何故,我有些不喜欢他,直觉告诉我,他很危险。
“就在前面,我要去找他了。”丢下这句话,我便匆忙跑开了。
七拐八绕,我仍是没能找到李世承,要命,这皇宫哪哪都是一个样,怎么才能走出去呢?
我绕来绕去,绕到了湖边,便止步停了下来,仔细说来,这潭湖水并无特别之处,吸引我驻足的是位于湖中心的那座小亭子。
那是一个六角亭,亭顶是晶莹剔透的琉璃瓦,瓦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五光十色的妖冶光芒,亭顶上的六个翘角分别挂着几张薄薄的玉片,微风一吹,互相碰撞发出“叮当”声,悦耳好听。
在我们漠北,湖水池塘什么的,本就不多见,更别说像这种精致的湖心亭了,那可是绝无仅有的。
我提起裙摆朝着湖边走去,待漫过一段樟子松栈道后,来到了湖中心的六角亭。
已是初冬的季节,亭外满池的莲叶开始落败,深深浅浅地浸在湖水里,枯黄弯折的残荷茎叶有些还在水面上,有些已经随着莲蓬沉到了水下,留在湖面上的也只剩下些千折百回的茎杆。
这一湖的残荷,倒也别有韵味,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自有一番萧索之美。
我倚栏而坐,伸手折了几株莲蓬,心想,如果有人能把我嵌入其中,绘一幅残荷美人图就好了。
远处传来了嬉笑声,我循着声音望了过去,发现是李元初与璃洛公主,呃不,应该说是太子与太子妃。
两人正撑着船在湖面上划行,船舱里堆满了莲蓬,两人窝在一起开心地笑着,一袭出尘的白衣和一袭飘然的红衣在风里流动着,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一对璧人,绝美如画。
胸口又开始隐隐作痛了,我瘫坐在栏干旁,拧眉捂着胸口,不明白身体为何会差到这种地步!
自打来到永朝后,我常没来由的胸口发痛,难不成真像夭夭说的那样,我与这永朝犯冲?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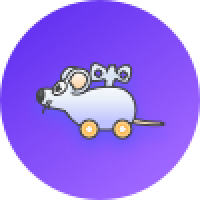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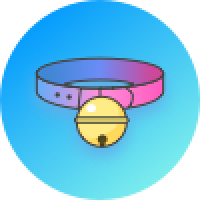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