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
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
愁聚眉峰尽日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
西湖风光,天下闻名。
时人有云:“北土名园,莫多于都下;南中名园,莫盛于西湖。”。这是说西湖一带,别墅宅邸,星罗棋布。不论大小,皆精妙绝伦,冠绝江南。此间就有一处园子名为“谢庄”——很明显,这园子曾经的主人姓谢,其祖上本是个富商。可惜自古富不过三代,到了这一辈,几个谢氏子孙斗鸡走狗吃喝嫖赌无一不会,败光了家产便急着变卖祖宅,正好叫那时走马上任的杭州知府冯正则捡了个便宜。这谢庄邻着西湖,里头凿池引水,聚石为山,松墙竹径,移步易景,隔着石窗便能一览西子湖光山色,让冯府台直呼此乃瑶台仙境。
冯府台膝下两子三女,除了夭折的二儿子冯钦和嫡长女冯永宁,其余皆为妾室所出。他虽无大才干,但平日勤政爱民,其原配夫人林氏又早早难产而亡,以至于在丫鬟仆妇手上养大的冯大小姐自小无人教导规矩,被纵出了个无法无天刁蛮泼辣的性子,在家中打骂下人,出了门则罔顾礼节,小小年纪便恶名远扬,和她那个温柔娴静的庶妹冯永盈有天壤之别。
这天,还是大清早,梧桐斋内却人声鼎沸。原来是冯大小姐丢了簪子,正气急败坏地罚着房中几个丫鬟。丫鬟们跪在院子里,哭声求饶声震天,不一会板子上了,拶子也夹了,其中几个胆子小,挨不住,交代了自己曾见过二小姐冯永盈戴过一支一模一样的。经这一点醒,冯大小姐立马想起之前她看到这簪子时两眼发光,垂涎欲滴的样子,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也没多想,认定了冯永盈就是那贼,领着人马风风火火地赶赴战场。
刚到翠微阁,姐妹俩还没说上话,冯大小姐就当着冯永盈的面砸了一尊青花竹枝梅瓶。瓷片像水花一样溅开在冯永盈的脚边,吓得她缩了脚尖进裙摆里。
冯永盈吓得唇牙打颤:“长姐,你这是做什么?”
“好你个冯永盈!我房间里丢了东西,你却在这里赏景?”冯大小姐用眼刀挫她,命令手下的丫鬟仆妇,“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搜!”
一众丫鬟仆妇得了令,如入无人之境,把碍事的冯永盈推搡到一边
冯永盈踉跄了一下:“长姐丢了什么东西?为何要搜我的房间?”她没明白冯大小姐丢了东西怎么自己就不能赏景了,这世间有这样的道理吗?
冯大小姐的贴身侍儿云蟾给她解释道:“大小姐丢了支心爱的簪子,怀疑府上有人手脚不干净。”
翠微阁几个仆妇堵在门口,七嘴八舌地辩解:“这不可能,我们房里的人不可能干出这种腌臜事。”
“哟,你们说没有便没有?”云蟾吩咐了几个下人,“你们都几个手脚麻利些,一处都别落下。”
冯永盈房中的人寡不敌众,眼看着冯大小姐领着人翻箱倒柜,在旁哭闹成一团。
闹腾了半天,有个眼尖的丫鬟弯了腰看到房中那八步床下有件戗金彩漆龙凤纹漆盒,招呼了云蟾:“云蟾姐姐,这床底下还有个东西!”
冯永盈大惊失色,慌不迭去拉扯那个丫鬟:“这不能动!”
冯大小姐气笑了:“为什么不能动?不会是赃物吧?”
“总之不能动!”冯永盈双目含泪,意态坚决。
“给我起开!”冯大小姐一把推开她,从床底下拖出那只盒子。
冯永盈就差没给她磕头了:“长姐!”
打开那小匣子,果真见里头躺着一支金累丝镶宝簪子。
“你个小贱人!怪不得那天有人看见你戴了这支簪子,原来早就得手了?”她扬手一巴掌将冯永盈打倒在地上,扇得她那满头的珠翠哗啦啦掉了一地。
“住手!”
原本房中哭的哭,闹的闹,骂人的骂人,一下子全被吼住了。众人闻声一看,来人是老爷冯正则,一身家常杭绸道袍,头戴着平定四方巾,显然是匆忙赶来,尚且还喘着粗气。
见自己的心肝宝贝瘫在地上,冯正则心猛地一揪,质问大女儿:“冯永宁!你做什么!”
冯大小姐有恃无恐,冷哼道:“父亲,冯永盈这贼没廉耻的货居然偷窃女儿房中的物件,这是她罪有应得!”
“女儿没有!”冯永盈头摇得如拨浪鼓,豆大的泪滴洒在地上。
冯大小姐一口哕在她脸上:“证据确凿,你这没槽道的行货子还狡辩什么?更何况那天所有人都听到你口口声声说喜欢这只簪子,你分明是觊觎已久。”
云蟾也跟着道:“是啊老爷,那天二小姐当着我们的面说自己很喜欢大小姐的簪子。”
冯正则看了看冯永宁手里的簪子,沉着脸问冯永盈:“盈姐儿,这是怎么回事?”
冯永盈垂丧着脑袋只顾着抹眼泪,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一旁的平嬷嬷恭敬道:“老爷,这簪子的确不是大小姐那支。这事原也怪我们盈姐儿,她那天看到大小姐新得的簪子便心下喜欢,就托着二门秦伍家的去城南的铺子也按着样子打了一支,没想到好巧不巧大小姐丢了簪子,这才生了误会。”
“胡说!”冯大小姐那飞扬跋扈的神情瞬间冻结在脸上。
冯永盈委屈地抽噎:“父亲和长姐若不信,大可叫了秦伍家的来。”
冯正则使唤了一旁的小厮:“冯禄,去叫秦伍家的来。”
不一会冯禄就领着秦伍家的过来。那妇人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了一遍,原来冯永盈的确所言非虚。
如霜打的茄子,冯大小姐再没了那一开始的气势:“不可能!这不可能!”
“难不成秦伍家的还会帮永盈撒谎不成?”冯正则气得了拍桌子,桌面上的茶盏被震得叮当响。
冯大小姐颤抖地指着冯永盈:“那你刚才装模做样不让碰那匣子给谁看!分明是做贼心虚!”
“长姐这是什么话。我自知身份不如你,不配和你拥有一样的东西,我是怕你见了我打得那簪子,会惹得你生气。再说了,我再低贱,也是要脸的。”冯永盈似是说道痛处,呜呼一声又哭起来,“都是永盈的错,谁叫我是那庶出呢……”
“够了!”冯正则一吼,走到冯大小姐面前,“你这孽障,平日无故欺压庶妹我也忍了,如今却越发厉害了。这副目中无人的泼辣样子可是对得起你故去的母亲?”
冯大小姐被戳到心窝子,一下子红了眼:“您还好意思提我母亲?”
“你!”冯正则气不打一处来,扬起手掌就要打她,却她一双眼满是怨念地瞪着自己,不由得手哆嗦了下,终究没落下去,“你去给我跪着,没我吩咐不许起来。”
于是冯大小姐在梧桐斋的院子里跪着。秋夜凉如水,冻得她直打哆嗦。冯正则只嘱咐了她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才让起来。她一向气傲,赌气死撑着,最后身子一歪晕倒在青石板上。
大战告捷,朱姨娘拿着两个煮熟的鸡蛋在冯永盈的脸颊上翻滚。
冯永宁下手不轻,冯永盈原本白嫩的脸上烙着五根鲜红的指印,一碰到那处就疼得她倒吸一口气。
“今天委屈你了。”毕竟是亲生女儿,朱姨娘说不心疼那是假的,但那眼角眉梢的笑意是掩不住的——冯永宁的霉日便是她的好日子。
“女儿不委屈。”冯永盈倒很是乖巧,她知道自己不比胞妹永佳来的机敏灵巧,在朱姨娘面前没法出谋划策,便努力向贴心小棉袄的方向发展。
“好在佳姐儿机灵,及时去喊了老爷来。”
三小姐冯永佳坐在一旁的绣墩上剥着新鲜的涌泉蜜橘,得意道:“亏得是冯永宁蠢到了家,这么容易就上了套。看样子啊,她又有几天苦日子要过了。”
“苦日子?”朱姨娘笑容冷了下来,“人家可是正经的嫡出,再怎么苦也比咱们来的风光。”
冯永佳见说错了话,忙说:“娘别急,总有一天冯永宁会被咱踩在脚底下的。”
“但愿吧,”朱姨娘把滚过的鸡蛋丢给贴身丫鬟婵娟,抱起了脚边的西施犬在怀中摸了摸,“对了,帔儿那边可想好由头了。”
别看这帔儿年纪不大,办事却挺利索,不声不响地就把那支簪子藏得没了影。再加上冯永盈前些日子装得对那簪子垂涎三尺的样子,还特意去打了一支一模一样的,戴在头上往人前一晃悠,冯永宁这脑子缺根筋的不上钩才怪。这位大小姐性格就像个炮仗,一点就炸,那能静下来摸索出这其中关系,估计到现在都没缓过神来。
冯永佳把剥好的橘子递给朱姨娘:“娘放心,冯永宁那傻大姐好糊弄得很,随便找个由头便搪塞过去了。
*
湘帘微垂,窗明几净。
一只龙耳三足香炉正飘着袅袅烟气。窗边靠着张黄花梨木梳妆台。灵芝卷草花叶纹六足高面盆架立在墙角,对面是一座冰绽纹透格门柜。蜜蜡海棠花盆景摆在一方有束腰带托泥香几上。墙上缀着幅烟笼玉树图。再往外便看不到了,因为一道紫檀木边山水画围屏摆在那里。
这是冯永宁的闺房,可那张榉木打洼万字纹拔步床上躺着的却再也不是她了。真正的冯永宁,就似那一缕薄烟,上黄泉下碧落,不知飘去了何方。
盯着头顶那一抹子沉香色的承尘,永宁心情复杂。
现有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好的是自打她昨天稀里糊涂过马路被车撞后,在一本小说里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书讲的是某朝中后期,男主程敏行和杭州知府家的小姐永盈相恋,两人情比金坚,克服了重重磨难,终成眷属。程敏行不但金榜题名,累官至户部尚书兼内阁首辅,还和永盈成了一对如花美眷,传为一段佳话。
既然是小说,肯定少不了一个为非作歹令人唾弃的反派。
那坏事就是——她穿成了反派女配冯永宁(永宁那时候还好奇为何这女配名字和自己一摸一样)。书中这个女配脾气暴戾,心思歹毒,身为姐姐却百般刁难女主。这女配一门心思想嫁给男主,甚至不惜污蔑他毁了自己清白,得偿所愿进了程家之后,又饱受男主的冷落,抑郁成疾,不久撒手人寰。
永宁先前强烈谴责过这个女配,没想到如今自己转身成了她。
真是让她哭笑不得。
她还保留着上午那场闹剧的记忆,在床上翻了个身,一遍遍捋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太巧了,她的簪子不见了,冯永盈那儿就多了支簪子出来。
又翻了个身。
而且,既然冯永盈说了怕自己生气,为什么又要唯恐天下人不知地戴着簪子出去晃悠。
“小姐,”云蟾端了汤药上来,打断了永宁的思绪,“奴婢伺候您喝药吧。”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永宁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咳咳,我自己来吧。”
“啊?”云蟾不知所谓的抬起脑袋。
永宁一把端过那青花缠枝苜蓿纹碗,望着里头黝黑的汤药,皱着眉头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
云蟾眼瞪得和铜铃似的,要知道这个吃不得一点苦的大小姐什么时候喝药这么爽快过,每次不都是骂骂咧咧的。
“小……小姐,吃个金丝枣去去苦味吧。”
永宁这副身躯早饿的眼冒金星,把整碟的枣子全吞了下去,连味道都没尝出来,就觉得喉咙一胀——是噎住了。
云蟾忙拍着她的肩膀给她顺气:“小姐,您慢着点。奴婢让厨子整治些菜上来。”
永宁催促她:“快!去去去!”
一道道菜盛在一套青花凤穿花纹瓷盘中端上来——金陵盐水鸭,清炖笋鸡脯,火肉白菜汤、春不老炒冬笋......永宁狼吞虎咽,一阵风卷残云,叫几个丫鬟婆子看得面面相觑。
大户人家生活就是精致,碗小如醋碟。永宁连吃了几碗饭才觉得干瘪的肚子鼓了起来。
“姑娘,老爷说了,罚跪免了,可得禁足两个月。”罗氏上前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
照着以往,冯大小姐肯定要发一通大脾气。
“知道了。”可如今的永宁只豪迈地打了个嗝,又回榻上躺着了。
她记得书中这个罗奶娘,是林氏生前就选好的人,对冯永宁最是忠心不过,可这位大小姐从小只觉得这个奶娘啰嗦,做什么事她都有异议,最后随便找了个由头打发了她去了偏远的庄子养老,从此再无音讯。
夜里三更天,城内的更夫打了梆子。
几百年前的杭州城,没有后世的喧闹,夜静如水,却更显得那一阵阵的犬吠突兀,永宁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只好叫了房外守夜的丫鬟进来。
那丫鬟支支吾吾道:“小姐,那是朱姨娘养的狗。翠微阁离这儿近,难免会吵到小姐。“
朱姨娘!永宁一个激灵,险些没从床上翻下来,就是书中那个骄纵恶毒的妾室?书中的朱姨娘平日里装出一副慈母的样子,实际上暗地里对冯永宁下了许多绊子。据永宁推测,原身嫁入程家被害流产,以致不孕也是这位朱女士的手笔。
“这怎么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你去找朱姨娘说说。”
守夜的丫鬟踟蹰着不肯去。
永宁冷笑着反问:“怎么,朱姨娘有那么可怕?”
“不是的小姐,只是朱姨娘最宝贵那只狗,恐怕……”
永宁老大的不爽:“难道我连狗都不如?”
那丫鬟委屈地嘟了嘟嘴:“小姐您忘了吗?您以前被那狗咬过。老爷因为姨娘在他面前哭了几声,结果根本就没追究……”
好吧,看起来在她爹眼里自己还真不如朱姨娘的一条狗。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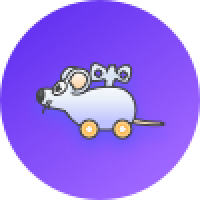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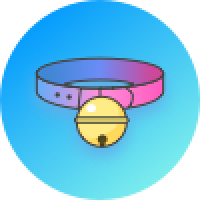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