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散学钟响时。
书院外的马车,鳞次栉比,占据了整条青云街巷,这其中的先后排序,讲究的自然是师者为先,其次便是家世地位。
一时间,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景象浩浩荡荡。
楚冬青散学时,从来都不急,因为路上马车实在太多了,冒然置身其中,实属不明智。
走得晚的,还有钟博士,因为短视,别人与他打招呼时,他总是不能及时回礼,为了不失礼于人,他便选择在人几近走光后,才离开。
二人的交集,便是这般机缘巧合。
壬寅班,二人对案而坐,钟博士执卷为少年解惑,前者孜孜不倦,后者拨云见日.
不久,书本中的疑问便一一被解答完。
楚冬青当即又讲出心中的纠结。
钟博士一边听着,一边端详着眼前的少年,不禁有些恍惚,回忆起往昔,同样是在这座书院,同样是疏离同窗的少年。
当年,钟渔在书院求学时,只知埋头读书,又因不善言辞,其间不曾结交任何朋友。
但是这位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生,同窗不喜与他来往就算了,连书院的博士每每遇见他,也唯恐避之不及。
这位书痴,在师生眼中,就是一位怪胎,一位喜欢请教博士疑难,能将问得先生哑口无言的怪胎。
因为读的书太多,且又杂又偏,书中的疑惑,书院的博士时常闻所未闻,不知如何解答。
那些被为难住的博士,解惑不了时,往往会板着一脸严肃的脸,指责道:“尽看些无用之书,自毁前程。”
当楚冬青讲述完时,钟博士笑了笑,问道:“其实你并不讨厌谷博士,对不对?”
少年一怔,心下为之一喜,更加笃信,先生能为自己排忧解难,同时抵不住心中好奇,问道:“先生如何知晓,学生并不讨厌谷博士的?”
“若你真讨厌他,只需顺着齐楼的意,将其换掉即可,又何必纠结于此?”钟博士回答后,又追根究底地问道:“谷博士常年那般羞辱你,你为何不讨厌他?”
楚冬青挠了挠头,淡然道:“不管是书院内,还是书院外,如谷博士这般的人,其实很多,他们或多或少都抱有恶意,但这点恶意,还不足令学生怀恨于心。
况且学生以前确实愚钝,如今虽有了些长进,但学生有意藏拙,他们便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
先生曾教诲道,‘不知者无罪’,所以学生从不曾怨恨过他们。”
钟博士听罢,怅然不语,眼前的这位懂事的少年,他很器重,但也很无奈,心中各般情绪,终是化为一脸苦笑,抚慰道:“终会苦尽甘来的。”
楚冬青瞧出了先生的心思,粲然一笑,反过来安慰道:“其实糟糕了一点,但学生并不觉得很苦。”
钟博士莞尔,心扉畅然,对少年的赏识,愈发深厚,坚信道:“如何解决此事,想来你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
“先生莫非能洞察人心?”楚冬青诧异道。
钟博士蓦然起身,话锋一转,“时辰不早了,边走边说。”
他静立讲堂门口,等楚常青收拾好书囊,当后者趋步跟上时,言归正传道:“且说说你的主意?”
楚常青略微酝酿了一下,便道明自己的想法,“谷博士身为师长,品行纵然有缺,学生究其错即可,但僭越去惩处他,实属不应该。”
“你觉得齐楼做得不对?”钟博士质问道。
楚冬青心下黯然,回答道:“齐楼属于好心,但撤换掉谷博士,却未必是件好事。”
钟博士细细说道:“谷博士任教十余载,品行如何,书院山长怎会不知?
外人都说是因为他女儿是裕王的宠妃,故而山长不敢将其怎样,这未免太小瞧书院山长了,虽说山长官职只是祭酒,品秩不高,但他却是晏国儒生之首,哪怕面对当朝皇帝,也是不卑不亢。”
楚冬青对此颇为惊讶,虽说晏国是以儒学治国,但在这战事频发的乱世,读书人的地位,却远不如武将。
“山长大人若真想撤换掉谷博士,莫说是裕王,就算是圣上,也不会有任何异议。”
楚冬青似懂非懂,问道:“所以,山长也并不讨厌谷博士?”
“在山长眼中,一个潜心究学问的人,哪怕小节有失,也无妨,此之谓,不拘一格降人才。”
钟博士蓦然回首,眼中除了敬佩之外,也有悲哀,书院的博士,品行兼优者,实在太少了,要不然老山长也不必如此。
楚冬青循着先生的目光望去,听说在书院的深处,坐落着一间书斋,书院山长平日便深居于此。
钟博士收回目光,继续一边走,一边说道:“你可知,先生当年在书院修学时,最喜欢的师长是谁?”
楚冬青迟疑道:“莫非是谷博士?”
钟博士颔首笑道:“先生年少读书时,每有不懂之处,便会询问师长,但因为问题过于刁钻,总是将师长们给问蒙了。”
“谷博士能回答上?”楚冬青问道。
钟博士摇头道:“谷博士也常被问得捉襟见肘,不过谷博士善于深究,回答不上便记下,事后钻研,等弄明白之后,再来讲解先生听。”
“如此看来,谷博士师德也不算太坏。”楚冬青笑道。
钟博士沉默不语,不置与否。
楚冬青心中的纠结,已然化解,恳求道:“先生能否将此中原委,告知谷博士,好教他莫要再为难学生,这样齐楼便没有理由将谷博士撤换掉。”
钟博士再次驻足,停在九层台阶前,一口答应道:“可以,但先生有一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楚冬青不曾多想,也很爽快地回答道:“先生有何问题,但问无妨,学生定不相瞒。”
钟博士笑道:“你何时食气成功的?”
楚冬青听罢,满心讶然,愈发觉得先生不可思议,但旋即又垂下头,如同犯了错的孩子般,低声道:“学生并不是有意隐瞒先生的。”
钟博士拍了拍少年的肩膀,安抚道:“先生并没有责怪之意,把头抬起来,此乃好事,当高兴才是。”
“先生,何时发现的?”楚冬青好奇道。
“去年腊月初一,一阵猛烈的寒风破窗袭来,满堂书本翻飞,场面十分凌乱,唯独你不动如山,书案上亦是安然不乱,那时先生才初见端倪。”钟博士笑了笑,继续说道,“之后,先生也曾有意无意地试探过,最终才断定你已食气成功,成了一名炼气士。
至于你隐瞒的苦衷,先生自然明白,一位遭同窗嫌弃,且不被瞧得起的人,如果突然有一天咸鱼翻身,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需要被仰视的存在。
迎来的,往往不是祝贺与羡慕,而是更加的厌恶。
先生虽没有揭穿你,但并不代表先生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正如你口中的齐楼一般,好心未必干的就是好事。
你是一根修道的好苗子,先生作为你的道师,眼睁睁见你荒废自己,甚觉痛惜。”
楚冬青脸泛愧色,低声地解释道:“学生自食气以来,有瞎捉摸着修行,且每日不辍。”
钟博士无意责备,虽说修行在个人,但没有师父的点拨指引,无异于闭门造车,况且没有师承的炼气士,很难修炼高深的道术与道法。
他很清楚,楚冬青所谓的修行,只是简单的驭物之术罢了,连道术都称不上,不管如何苦练勤修,也难为突破其桎梏,除非他能自创道术。
但自创道术何其之难,国教太玄宫,作为晏国道统,已有近千年,但掌握的道术,也不过百数,史上自创道术者,最年轻的也过了半百之龄,所创道术,还是一门最低等的末流道术。
一根好苗子泯没于无人知晓,钟博士无话可说,但被他发现了,就绝不能视而不见,更何况,这株好苗子,还是他本就器重之人。
“那且让先生瞧一瞧,你修行的成果如何?”
钟博士已经打定了主意,若楚冬青表现太糟糕,他便要插手后者的修行,收其为首徒,令其拜入太玄宫门下。
楚冬青问道:“先生可是要试炼学生?”
钟博士颔首示意,环顾四周,眼前只有两棵古木罢了,当即便冒出了一个想法,但细思之后,又觉得不妥,那个法子对楚冬青而言,太过勉强。
楚冬青见钟博士陷入沉思,心中反倒生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想法,开口道:“先生,学生有一法子。”
“说来听听!”
“将这两株大树当做书册,叶子当做纸张,先生化气机为风,撼动树叶,学生如去年腊月那般,抵住劲风,让叶片纹丝不动。”
钟博士一开始想到的,也是这个法子,但太难了,楚冬青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气海,去支撑他将气劲地落到杂乱无章的树叶上,还要力道要掌控得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有叶片掉下来。
当他听完这个想法后,内心十分讶然,因为这是一个巴蛇吞象的法子,口气之大,像极了自称狂人的楚常青。
但眼前的少年,虽与楚常青相貌相近,但兄弟俩的性格却截然相反,一个张扬,爱说豪言壮语,一个守拙,谨慎不妄言。
他很清楚,楚冬青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震惊之余,他愈发好奇,楚冬青的实力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你且去树下,在这,你会更吃力。”
楚冬青立在树下,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
钟博士旋即运转气机,随意一震袖。
忽然清风飒来,轻柔似水,吹得满树枝叶簌簌。
楚冬青全神贯注,体内气海澎湃,气劲附着在每一片树叶之上。
前一瞬还微摆不止的枝叶,霎时凝滞,这一刹那的光景,目睹之人,只觉时光停滞了一般。
钟博士眉眼含笑,虽然才刚开始,但楚冬青仅是自学,就能做到这一步,说明他的确下了苦功夫。
只见他大袖一荡,劲风呼啸,吹得人眼难以睁开。
郁郁青青的古木上,老嫩叶芽纵横,陡然猛烈一颤,十余片娇绿,不堪蹂躏,于浩浩强风当中,翩然落下,画面诡谲。
“不错!”钟博士不吝赞美道,少年有这般造诣,不单得靠苦修,还要有不俗的天赋才行。
欲试良玉,还须猛火。
钟博士抬手奋力一挥,袖中风如镰,所过之处,杂草割裂飞舞。
苍木之下,少年峭立独秀,孤身似旌旗。
风掠过,旧衣刿,只见落木潇潇,但转眼又依稀,一地零碎,却多是乱麻。
钟博士见状,敛袖收功,神色愕然,惊叹道:“什么傲雪花,这分明是株凌云木!”
楚冬青一脸疲态,习惯地自我菲薄道,“自己还是太弱了,一场简单的摸底试炼,居然弄得筋疲力尽。”
当他瞧见身上的白苎衣,已经散落成一地乱麻,忧愁之色浮上脸庞。
楚家清贫俭朴,少年的衣袍,皆是兄长遗留下来的,兄长的衣物本就不多,又因尸骨无存,设了一座衣冠冢,就更少了。
以至于少年一年到头,也就两身换洗衣物,如今毁坏了一件,难过虽说不上,但终归不是滋味。
白苎制的麻衣,哪怕珍藏起来,时日长了,也容易腐朽老化,何况这还是一件旧衣呢?
只不过,儿无衣,娘难眠,今后的日夜里,害了眼疾的老娘,又要拖着病躯,不分昼夜的挑灯纳新衣。
一念至此,少年就于心不忍,有些后悔,没听娘亲之言,莫要在人前逞风头。
只因这次提出试炼的人,是钟博士,所以他不想藏拙,倾尽了全力。
钟博士已经来到少年的身边,歉然道:“待会,先生赔你一件新衣服,若你穿不惯锦衣,便给你买一件麻衣。”
楚冬青很想婉拒,但一想到娘亲,却很难开口。
钟博士猜到他的心思,譬解道:“凡事不能一昧只求自己问心无愧,也得顾及他人感受,你那麻衣虽已老旧,但终归是先生损毁的,赔你一件衣衫,对先生而言,不过是小事一桩,这种小事又何必让先生自责呢?”
“学生蒙昧,谢过先生开解。”楚冬青也不矫情,行礼谢道。
钟博士招呼马车过来,笑道:“上马车,去买新衣!”
钟家马夫眼窝子浅,在此等候自家公子,只觉刚才莫名刮了一阵妖风,瞧不出其中的不凡。
车厢内,钟博士问道:“你也该说说,你究竟何时步入食气境的了?”
“十岁!”楚冬青如实回答道。
“十岁?你十岁那年,我才教你们吐息心法,也就是说,不到一年,你就成了炼气士,十岁的炼气士,纵观在晏国,乃至整个定今洲十六国,也是史无前例。”钟博士笑道。
楚冬青欲说道:“其实先生授法的当月,学生便食气成功了。”
钟博士哑然失笑,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这是一枚天生道种,绝不可任其埋没。”
“你平日都是如何修炼的?”
“干活!”
“干活?”
“对,家里要干的活太多,自从步入食气境,借助驭物之便,学生可以更轻松,更快地忙完家里活。
四年下来,活干多了,驭物之术运用的愈发得心应手。”
“世间万般奇技,神乎其神,皆始于手熟,此理言之轻巧,却行如积土垒山,篑篑艰辛,鲜有登峰造极者。”
钟博士满心感慨道,但有些话却又止于齿间,堂堂大司马之子,十岁便有干不完的活,在这世子皆贵的晏国,是何其讽刺。
“你应该知道,驭物只是炼气士的基础之术,而炼气士强大之处,在于道术与道法,要修习法术,就必须拜师于道门。”
一座道门的根基是否深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门派内的法术,只有掌握强大的法术,门派才可以兴盛,所以任何一个门派的法术,是不允许外传的。
食气境的修士,在修炼法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专研于驭物术,一方面是为了拓宽丹田气海,另一方面算是为了将来的修炼而筑基。
比如齐楼,哪怕已经是太玄宫的弟子,但也没有急于修炼法术,而是循序渐进的将基础练扎实。
但楚冬青的驭物之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今他修炼一门末流道术,已是高屋建瓴,远比一般人来的容易。
楚冬青只知道门法术的玄奥精妙,却对自身的实力没有清晰的认知,他以为自己离修炼法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殊不知,他的基础之深厚,以齐楼的天资,也至少要修炼个三年以上,但是,齐楼肯定不满三年,便会开始修炼法术。
在许多炼气士眼中,过于沉淫于驭物之术,无异于舍本逐末,轻重不分。
所以,几乎没有人会将驭物术,精进至这般地步。
“在修道方面,你的天赋极好,先生萌生了收徒之意,先生知道,你有顾虑。
但先生要告诉你,你有龙马之才,应当上青云才是,若自困于厩中,终将沦为肉马。”钟博士语重深长道。
楚冬青沉默不语。
钟博士不急一时,转念道:“你回去好好思虑,只要你愿意,随时可拜先生为师。”
......
孝字桥头,马车停了下来,楚冬青拜别了钟博士,便下了马车。
街道上,行人逐渐稀少,但悬榜的小亭处,却观者如堵。
楚冬青已经穿上了新衣,他从榜亭路过,对人群视若无睹,对悬榜也毫不好奇,但无意间,还是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关于悬榜的事。
“谁吃了雄心豹子大胆,杀人就算了,还敢投尸汝河,那可是诛三族的大罪!”
“说不定是自杀,贫苦家的孩子,家里人死光,活不下去了!”
“这可不是自杀,我听说,这是命案,还跟经丘书院有关呢!”
楚冬青默然地走着,并不关心悬榜之事。
路上总有一些行人,见到楚冬青之后,便会稍作停驻,很礼貌的朝他微微一笑,或是朝他哈腰行礼,更有甚者跪地敬拜,而这些人无一不是贫苦百姓。
楚冬青很清楚,那些人表达的敬意,并不是致给他的,而是给他的父兄,更多的是给他父亲楚原的。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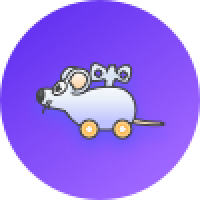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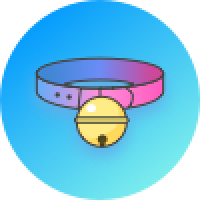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