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今洲有十六国,分南北两境,北境地域辽阔,有十四座小国,皆是以魔教为道统,常年战乱,民不聊生,诸国当中,就属庆国实力最为强悍,但多少年过去,乱战的局面却始终未变。
南境只有晟国与晏国,皆以浩然道教为道统,两国虽也有意荡平北方魔教,但每每出兵,形如散沙的北方十四国,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立马抱团,势力之大,根本难以攻破。
如果两国也结盟,兴许能有一战之力,奈何两国从立国之初,便是势如水火的宿敌。
定今洲最初是景国一统江山,只不过后来景国皇帝昏聩不明,荒淫无道不说,甚至还屠戮忠良,最终被权臣弑杀,并篡国改号为晟国,是时天下大乱,北方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
而晏太祖作为景国皇室宗亲,打着光复景国的旗号,与晟国打了一辈子的仗,结果没光复,反倒自立国号称帝。
至今,晏国与晟国依旧战时频发,结盟一说,几乎是遥遥无期。
晏国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不说,更是占据了定今洲最肥沃之地,按理说,应该具备平定天下的优势。
只可惜,这是雨泽之国,每年都是洪涝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肥沃也枉然。
此顽疾不治,晏国终究只能偏居一隅。
四十多年前,晏国岭南虞氏,有一位天生双脚残疾的大儒,向朝廷推荐了一位治水青年,青年名为楚原。
楚原幼年时,在一场洪灾中,家破人亡,流离至岭南,饿晕在残儒虞修的门第前。
虞家收养了孤苦无依的小楚原,让他成为虞修的推车书童。
聪颖的小楚原,深得虞修的喜欢,后者本愿将毕生学问,倾囊相授,只可惜,楚原志不在此,而是欲与天公奋斗,解决晏国的沉疴——水患。
虞修仍是借助自身的关系,不余遗力的栽培楚原,并动用虞氏的人脉与及权势,将一介草民的楚原,举上了京畿水令丞的位置。
满腔抱负的青年,意气风发,赴京上任后,更是务实肯干,他施长技,献良策,凿运河,修百渠,通四渎,励精图治了三十余载,壮志将酬。
晏国之水患,日渐平息。
当年俊朗不凡的青年,如今不过不惑之年,但已经满头华发,衰老的十分明显,但也凭借着千秋盖世之功,从寒门跻身至士族,且步步高升,最终被破格擢升至大司马,位列三公之一。
楚原虽位极人臣,但他为官十分清廉,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实乃贤臣之表率。
以前在别人眼里,治水之官虽然吃力不讨好,但却是一块肥差,因治水吞金销银,耗资极大,随便贪污个零星一点,便可一生富贵无忧。
然而,楚原不但没有贪污受贿分毫,还将皇帝嘉奖他的赏赐,尽数投入治水当中,连自己的俸禄,亦是如此。
刚开始朝廷有不少人盯着他,认为他不过是假正经,过些时日便会露出狐狸尾巴,但是最后那些怀疑他的人,皆被这位能臣贤臣给为之折服。
这也是楚家清贫的原因。
楚原在晏国的威望之高,无人能及,当然,这种威望更多的是体现在老百姓的心中,至于在士族眼中,不过是一位能治水的能人罢了。
祜来坊有一座寻常的老宅院,简陋的门面上,挂着一面粗制滥造的匾额,上面的文字并非篆刻,而是有墨笔书写的“大司空府”四个字,笔法随意,字迹朴素,府苑的围墙上,攀附着的凌霄花树,枝繁叶茂,颇显清雅。
这便是楚冬青的家,一进家门,他便大声朝娘亲的屋内喊道:“娘亲,虎头回来了!”
屋里先是传来一阵咳嗽声,然后是一声的虚弱回答,“我儿回来了呀!”
楚冬青推门进屋时,见娘亲正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连忙快步上前搀扶。
苏寓娘抓扶儿子的手臂,手中的感觉明显不对,有眼疾的她,不由凑近细看了一下,疑问道:“我儿怎么换了一件新衣?”
楚冬青随即便将今日发生的事,娓娓道给娘亲听,当然,那些让娘亲担忧的事,自是不会提及。
苏寓娘听罢,叹息道:“你兄长自小聪明非凡,结果到头来,却断了卿卿性命,别人养子望成龙,娘亲只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终老。”
“娘亲不希望我拜钟博士为师?”楚冬青问道。
苏寓娘摇头道:“虎头,这世间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爹这一辈子拼了命也想干的大事,并非治水这一桩,在他有生之年,治水成功之后,如果尚有余力,他必定会去完成虞先生的遗志,到时将是与晏国所有的世家为敌,他们绝不能容忍楚家出天骄之子的。
你阿兄之死,便是如此。”
说完,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楚冬青见状,旋即心软道:“孩儿听娘亲的话,不拜钟先生为师。”
自从楚常青死后,楚家只剩下这母子两口相依为命,至于楚原,忙于治水,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就算回来了,也只是小住一两日罢了。
楚原就是个甩手掌柜,对家庭没有付出过任何东西,楚家完全就是靠苏寓娘一个人支撑起来的。
一个女人既耕又织,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楚冬青小时候曾听阿兄讲过,娘亲年轻时也很美,虽说不上花容月貌,但又清丽动人。
而今躺靠在床上的娘亲,白发垂榻,形如枯槁,脸色黄土,凹陷的双目黯然无神,显然这不是年老色衰所致,而是受痨病的摧残。
楚冬青见过娘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也见过娘亲因为阿兄的死,整日以泪洗面,哭坏了眼,也见过她因染上肺痨,病倒在地。
楚冬青从小便一直很听娘亲的话,哪怕心里有万般不情愿,但他也绝不会违背娘亲的意愿,在这世上,有些东西或许值得去追求,但有些东西更值得去守护。
三年前,娘亲的病还不算严重,根本称不上病危,但那个时候,他便开始去孝字桥祈福,因为肺痨是药石无医的不治之症,病情只会随着日子的增长,变得越来越严重。
肺痨之症讲究气顺,如果违逆娘亲,必将加重其病情。
这便是楚冬青的顾虑。
服侍娘亲躺下后,楚冬青就得开始忙活了,挑水劈柴,煎药熬粥,破竹编筐,给院子里的小菜苗捉虫浇水,喂喂鸡,打扫庭院,并将院中剩余下的一点空地,翻一翻土,种一些娘亲喜欢的花卉,最好是香气浓郁的那种,这样娘亲卧在床上,也可以闻到......
家中的杂七杂八的活,楚冬青已经干了四年,早就娴熟了,并且依仗着驭物术,他可以一心多用,同时忙几样事,力道也能够掌控得极有分寸,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他长达四年的磨砺,才修炼出来的。
因为不曾正经的修炼过驭物术,所以楚冬青才会不清楚自身的实力究竟如何。
夜里,楚冬青抄完那一百遍《将我》,却并有直接入睡,而是从床榻的夹层中取出一本书,这是他几天发现的,书是阿兄写的。
封面上书写着四个大字“神京札记”,三个小字“楚狂人”。
楚常青的名称很多,及冠时,他爹取的表字为“采葵”,但他自号“狂人”,而宣安城的老百姓更喜欢称他为“麻衣郎君”。
除了这些之外,他在上巳评还有两个很响亮的花名,璞玉榜时,他便有了四字花名“神勇公子”,圭璋榜时,皇帝更是御赐了花名“大晏於菟”。
顾名思义,这本书是阿兄的日常手札,里面记载的十分杂,既有他经历过的奇闻异事,也有他听闻过古怪之事,自从无疑间发现这本书,楚冬青便被深深吸引。
宣安城很大,但打小就不聪明的楚冬青,去过的地方却很少。
因为娘亲告诉过他,只要规矩本分就不会犯错,不犯错就不会招人嫌弃。
楚冬青将这番话奉为圭臬,一直恪守着,但长大些后,发现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被人嫌弃,其实往往并不取决自己,而是取决于对方,哪怕你什么都没做,对方瞧上你一眼,便起厌恶。
虽然这本书他已经粗略的阅览了一遍,但仍忍不住想多看几遍,宣安城有许多他闻所未闻的事物。
在外,规矩的少年,也会按耐住躁动的心,从不哪怕心猿意马,更不会干逾矩之事,但在家,观览《神京札记》时,却难以克制心驰神往。
其中有些神奇的地方,令楚冬青留下深刻的印象。
忠字桥的百樵市,是斩首刑场的,那有一滩数百年不凝不化的鲜血。
据说是一位大忠臣斩首时,洒溅出的,他在行刑之前,曾留下遗言,“枉死之臣,死后目不瞑,血不凝。”
此后,每有忠臣枉死,其血便会汇聚到一起。
这滩鲜血也就被老百姓称之为“忠臣血”,每次忠臣被问斩,朝野上下舆论滔天,当代皇帝难辞其咎,只好下罪己诏安抚臣民。
所以没有如山的铁证,不到万不得已,皇帝都不会轻易斩杀有贤名的臣子。
即便如此,当初不过一小酒杯的鲜血,如今已有盈盈一大盆,可见枉死的忠臣委实不少。
朝廷当然试过除掉那一滩血,只可惜,各般手段层出不穷,却无济于事。
那滩忠臣血,一直有太玄宫的道师看守,虽说是忠臣流下的血,但已被天地浊气所污染,隐含着煞气,寻常人若久视之,便会变得狂躁,有嗜血的冲动。
忠臣血既非纯粹的邪物,也非祥物,因为它出自忠臣之躯,蕴含浩然正气,但同时它又含有死者的怨念。
阿兄曾去过百樵市,亲眼目睹了那滩忠臣血,血红鲜鲜,触目惊心,在他内心幽深之处,一团不知名的火,忽然死灰复燃,识海霎时殷红似血,他如孤舟一般飘荡于惊涛骇浪的血海中,倾覆只在一瞬之间,在血海将其吞没之前,他当即收回眼,惊惶离去。
阿兄第一次感受到难以扼制的恐惧,那是一种即将迷失自我的恐惧。
阿兄在札记表述道,“忠臣血如同一枚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觉醒之门,不知是好是坏。”
在俭字桥的一户百年老宅,其堂屋高挂的辟邪镜中,总会无端地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景象。
有人曾从中见过,数不尽的白衣男女,当空御剑齐飞,遮天蔽日,犹如蝗虫过境;
也有人见过,奇禽异兽搏命厮杀,打得天摇地动,山河破碎;
也有人见过,一块黑色巨石上,长着无数张人脸,面目狰狞可怖,哀嚎声此起彼伏,但巨石之下,却盘坐着一位年轻僧人,一手敲木鱼,一手掐珠念经。
二者犹如弥天黑夜与青灯豆火一般,泾渭分明。
......
此镜过于诡异,后来被太玄宫收藏,并取名为“蜃镜”,自此非一般人,无缘观览此镜,且观镜者必须将镜中景象如实告之。
阿兄对蜃镜十分好奇,曾去太玄宫,求一观此镜,并被欣然准允。
在镜中,阿兄看见一位身穿黑甲,颈系赤色披风的将军,手持一杆红缨单刃戟,胯下骑着一匹锋棱骨瘦的神骏,从孤城之中奔杀而出来。
孤城外,千军万马,列阵以待,枪戟森森,士气如虹。
半空中,凌风蹈虚的炼气士,星罗棋布,各个意气风发,锋芒毕露。
而那一人一骑,挟牛斗之势,如经天流星,威风凛凛,夺人眼目。
将军舍生忘死,径直冲杀于大军之中,只见血肉纷飞,千军辟易,无人能挡。
最终,将军马踏于尸山血海之上,仰天大笑,遥望败军落荒而逃。
阿兄在札记如是写道,“世间当真有如此神勇之人,一人可挡百万雄师?
我辈唯有这般英雄风采,才算不虚此生。”
宣安城北的悬经寺,有一株古老的榆钱树,风调雨顺之年时,万木欣荣,唯独它病夭淡绿,但每逢灾年时,其他的树木长势都不好,但它又偏偏绿荫成盖,成了饥荒之年的救命粮,饥肠辘辘的百姓,吃完树叶,还要将树皮剥光吃尽,但光秃秃的榆钱树依旧能活下来。
百姓将其奉为神树,又因为它扎根于禅寺中,所以又被尊称为“菩萨树”。
以前楚冬青也听说过神树,但札记中却一桩更离奇的事情,阿兄曾去过悬经寺为娘亲祈福,并敬拜了神树。
当他起身时,忽然发现原本无人的神树下,却莫名地趺坐着一位绛衣老僧。
阿兄以为是寺院中的僧人,便没有理会,不料老僧反倒叫住了他,并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诗,“九世修罗望成佛,血海余孽犹未尽,莲花宝座无尘坐,灵犀一点不可夺。”
说罢,便凭空出现在阿兄身前,并在他眉宇间画了一个“*”的符号。
其间阿兄曾试图反抗,结果发现自己仿佛被下了定身咒一般,根本动弹不得,当符号画完后,阿兄只觉得眼前金光夺目,眨眼间,那老僧便消失不见了。
事后,阿兄曾问过寺院的僧人,描述形容后,得到的回答皆是寺中无此老僧,就在其将要放弃时,一个打扫寺院的小和尚告诉阿兄,他见过那个老僧,不过是寺院的画壁上。
壁画讲述的,是在大浩劫之前,一位云游的苦行僧传道的事迹,苦行僧最后坐化于悬经寺,而坐化的地方,便是榆钱古树之下。
那次的际遇,令阿兄百思不得其解,仿佛冥冥之中,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
在宣安城西南处郊外,有一座奇峰,孤零零地耸立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之上,陡峭的孤峰,宛如长剑,兀然插落在那,与四下的景物格格不入。
孤峰名为“独秀峰”,但宣安城百姓更喜欢称它为“折寿峰”。
独秀峰不高也不大,笔直竖立,瞧不出有分毫倾斜,山壁上怪石嶙峋,草木不生,只有一条石阶小道,盘旋而上,直至顶峰。
任何人凝视独秀峰,只觉得它虚无杳渺,明明山巅上没有云烟笼罩,但穷极目力,也无法一窥全貌。
一般人都不会去攀登独秀峰,并不是因为它过于陡峭,也不是因为它无利可图,而是因为那山太过邪乎。
山下一白昼,山巅一人生。
这便是“折寿山”之名的由来。
但凡登山之人,皆是朝如青丝暮成雪,仅一个白昼的光景,便渡过了一生的岁月,并且下山后,对山巅的所见所闻,全然不记得,并且次日便会寿终正寝。
那些上过峰顶的人,不论良善,回来后都出奇的安静,不喜不悲,问他们是否后悔上山,他们都是微笑不语,给人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
朝廷早就将独秀峰设为禁地,但总有一些想不开的,生无可恋的人,登峰赴死,寻求解脱。
阿兄没有上过独秀峰顶,但他却想一睹山巅的风景,在札记中张狂地写道,“他朝开山巨斧在手,定要劈倒这独秀峰,一览其真容。”
楚冬青观览了数页之后,便合上札记,将它放回原处,然后上床睡觉,但最近一躺下,就愈发想念阿兄。
他很小的时候,经常与阿兄同睡此塌,每晚阿兄都会哄他入睡,哄的方法也很简单,便是敞开窗牖,二人细数一窗星月。
兄弟两分工明确,他负责数月亮,阿兄负责数星星。
他数完一个月亮,便聆听着阿兄的数星星,在阿兄的细语中沉睡过去。
那扇窗很少被打开,今晚它开着,夜空中新月如勾,星汉灿烂,他学着阿兄,细数窗中的一颗颗星辰,数着数着便睡着了。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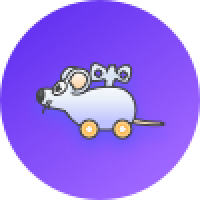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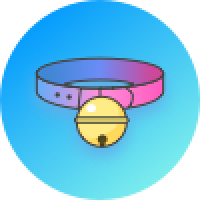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