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苏寓娘的房间,不时便会传出一阵难受的咳嗽声。
楚冬青的睡得很浅,每次都会惊醒,等娘亲的咳嗽停歇了,才会继续入睡。
每天的破晓之前,他便早早起床,将昨晚熬的药温热,并烙上几个饼,端放在娘亲的屋里头,然后去孝字桥祈福。
其实苏寓娘是不许出儿子去祈福的,因为她听闻孝字桥的传说,那是折子女的寿,延续父母的命,是一桩亏本的买卖。
但在这件事上,楚冬青却没有听从娘亲的意愿,三年来,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他都没有间断过祈福。
苏寓娘逐渐明白,自家二郎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傻儿子了,他心中已经有一杆权衡万事万物的秤,已经明白孰重孰轻,但他却视自己的娘亲为秤砣,哪怕是万般重要的事物,只要往后稍稍,便可会沉下去。
而这个当娘的,却要将他那杆秤给折断,让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卑微地活着。
她并不是愚妇,相反她很是深明大义,要不然她也养育不出楚常青那样的人中龙凤,只不过,她再也不想痛失爱子了,她得给楚家留下这仅剩的香火,哪怕变成自己讨厌的模样,也在所不惜。
楚冬青一路朝孝字桥走去,街巷上晦暗清冷,瞧不见几个行人,但半道中,他却遇见一个熟人。
确切地说,不是遇见,而是那人在等他。
这样的场景,在以往的日子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楚冬青习惯性地垂下头,装作没看见,不吭不响地从他身边路过。
那人也是少年模样,个头与楚冬青一般高,但体魄明显壮实后者,他倚靠在一堵墙上,微低着头,脸庞隐藏在阴暗当中,瞧不清神情。
二人形如陌路,皆缄口不语。
这种情况,以前是不曾有过的。
楚冬青的步伐不知不觉地放慢了些,似乎在期待着对方说点什么,虽然自己曾无次数拒绝过对方,但楚冬青却一直将其视为朋友。
那少年名叫顾当歌,是楚冬青在井泉书院蒙学时的同窗,也是第一位张口便要与楚冬青交朋友的人,而且是过命交情的那种。
当时的楚冬青虽然开窍了,但仍是虎头虎脑,比同龄的稚子相比,明显更愚笨。
顾当歌却迥然不同,他聪明伶俐,是难得的读书料,少年郎玩耍的把式,他也样样精通,因为家里是开铁匠铺的,六岁的他便浑身是劲,手上还耍得出几招像模像样的拳法,在书院里是妥妥的孩子王,唯独不好的,就是过于崇拜任侠,嫉恶如仇,爱管闲事,对于霸凌弱下的同窗,便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并美其名曰行侠仗义。
顾当歌小小年纪便以少侠自居,有一身的江湖气息,虽然只是少年,但谈吐十分老成,喜欢与人称兄道弟,无论是老少妇孺,只要张嘴便能与之攀谈上。
他喜谈麻衣客,犹爱吟唱楚常青那一句,“肩道义,轻生死,见不平,血溅之,生人杰,死鬼雄。”
出于对楚常青的敬仰,他对楚冬青也是爱屋及乌,很是照顾,没事便与之勾肩搭背,二人虽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
在井泉书院读书的两年,是楚冬青最快活的光景,那时阿兄还健在,娘亲也没病倒,在书院也有交到朋友,没人敢欺负他,大家都是穷苦出身的孩子,吃穿如同一辙,皆是烙饼与麻衣,从来不觉得有落差感,脸上时常洋溢着笑容。
但阿兄死后,这一切都变了。
老皇帝的一张圣旨,他去了经丘书院,娘亲日复一日的再三叮嘱,“万事皆隐忍,莫要意气用事,莫要出风头,莫要与人起争执......”
楚冬青一直很听话,只不过听话就意味着,不能再与顾当歌亲密如初,因为他从来就不安分。
面对楚冬青的冷淡,依旧满心热忱的顾当歌,起初难以接受,直到一次次的不期而遇。
前者总是孑然一人,面无表情,如同一具行尸走肉般。
后者身边却从来不缺同伴,之后更是新人换旧人,与之勾肩搭背的,是个楚冬青不曾见过的小胖子,他们有说有笑的模样,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
顾当歌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在一次次的偶遇之后,不知不觉间悄然释怀了,其实他一直明白,楚冬青之所以如此,其中必然有他所不知的隐情,但他又不明白自己究竟在计较着什么?
心中的芥蒂逐渐破除后,他便时常在这等楚冬青,自顾自地讲述着一些身边的事。
比如那个小胖子叫裴丕,是麻衣客裴缺的侄子;比如他一个人打趴了三个鱼肉百姓的市井无赖,后来被十个市井无赖吊在树上,扒掉衣服,用鞭子抽,打近百下他,皮开肉绽,但他从始至终没痛叫一声,只是不停地高唱着楚冬青的那句话;比如他那胆小怕事的瘸子老爹,不仅真去过北境,还是个深藏不露的武道高手,并传授了他一套拳法,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假把式,是正真能杀人的武技;再比如,他学有所成,便去寻仇,将那十个市井无赖都打成残废,并告诉楚冬青,对待恶徒绝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让他们吃尽苦头......
楚冬青每次都认真的听着,但只是听着而已,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
顾当歌却没有介意过,仍旧坚持不懈,每过一段时间,便会寻楚冬青说一会儿话。
直至去年,他突然告诉楚冬青,他要效仿麻衣郎君,建立新的麻衣客,重现麻衣客之辉煌。
其实他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自身实力并不过出彩,强行组建新麻衣客,不仅是贻笑大方,更会抹黑了麻衣客的名声。
后来,他终于觉得自身实力够了,便与裴丕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者与之不谋而合,也有意重建麻衣客。
至于第三人选,二人更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楚冬青的名字。
他们看中的,自然不是楚冬青的实力,况且他也不清楚其实力究竟如何,他看中的是其身份,麻衣郎君的胞弟,大司空楚原之子。
哪怕楚冬青不够惊艳,也无所谓,但有他在新麻衣客,就算是正儿八经的传承,而且借助楚氏的威望,新麻衣客也势必崛起的更快。
只可惜,顾当歌邀请楚冬青参入新麻衣客时,后者压根不想掺和这事,只是摇头拒绝,默然离去。
为此,顾当歌更加频繁地在这等着他,便是为了让他回心转意。
奈何楚冬青就像王八吃秤锤,铁了心,就是不答应,因为他很清楚,加入新麻衣客,非得把娘亲气死不可。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另寻他人,但寻了很久,也寻不到一个满意的寒门骄子。
新麻衣客也因为始终凑不齐三个人,便一直被耽搁至今。
近来,顾当歌都没有出现,今日他再次出现,楚冬青因为心怀愧疚,是故低头不语,但心中却不免暗喜。
只不过,往日里的顾当歌迎面便是侃侃而谈,今日是出奇的安静,简直就判若两人。
这不禁令楚冬青有些不安,止不住的胡思乱想,莫不是最近发生不好之事?
所以他放缓了脚步,在期待顾当歌开口,甚至最后,不知不觉间,居然驻足不前。
在脚步声渐停的那一刻,顾当歌开口了,说了一句很简洁的话,但语气十分低沉,仿佛在压抑着什么。
“第三人找到了。”
这应当是个好消息,但不知为何,楚冬青反倒愈发的不安,他背对着顾当歌,明明想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欲言又止,不知如何开口。
顾当歌似乎习惯了对方的沉默,问道:“你知道有人死在汝河了吗?”
此事,楚冬青昨日道听途说了一鳞半甲,只不过,他秉持一贯的作风,既不好奇,也不关心。
偌大的宣安城,近乎每天都有人被害,但很少被人重视。
昨天悬榜处之所以观者如堵,只因那人死在汝河,是一桩能惊动皇帝的命案。
然而,这与他却毫不相关,因为他除了流露出无用的同情之外,便一无是处。
顾当歌攥紧拳头,反身砸在墙壁上,一个寸尺深的拳印清晰可见,他悲愤道:“死的就是他!”
楚冬青听罢,觉得很是惋惜。
这对顾当歌而言,确实打击不小,也难怪他会如此气愤。
但对楚冬青而言,却很难感同身受,他试图安慰下他,但转念间,又觉得会适得其反,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毕竟,如果不是楚冬青一直拒绝加入新麻衣客,兴许就不会有这么一档子事,顾当歌也就不会如此悲愤。
既然自己于对方并无任何有益可言,楚冬青略微收拾了一下心情,便重新迈开步伐。
顾当歌侧目望向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怒不可遏道:“你就真打算装聋作哑一辈子?”
“你就一点不好奇那个人是谁?”
“你认识他!”
“他是雨生,雨生死了!”
最后一句话,犹如惊雷灌顶,炸得楚冬青头皮发麻,步履不停的他,一脚悬空,迟迟不见踏下。
“昨晚,贼捕掾去他家抓人,他娘听闻雨生死了,当场气绝身亡,他妹妹被抓进了大牢,择日问斩。
罪名是雨生自尽于汝河,动摇晏国之根基,诛满门。”顾当歌说罢,又一拳狠狠地砸在墙上。
楚冬青愣怔住了,如坠冰窟般,心身皆寒,许久才回过神,他将那只悬空的脚缩了回来,转过身,满脸仓皇,难以置信道:“不可能!绝不可能!雨生怎么可能自尽?”
“你骗我对不对,那个人不是雨生!”
顾当歌第一次见到楚冬青这般神情,不禁想起雨生每每谈及楚冬青时,总会眼笑眉开,一脸敬佩,像极了自己敬仰楚常青的模样。
只是他一直想不明白,雨生究竟钦佩楚冬青什么,二人关系又为何这般要好。
他原本想狠狠地斥责楚冬青一番,但此刻却说不出任何狠心的话,转而将自己知道的案情,尽数告诉对方。
“你与雨生应该认识很久了,他为人如何,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我也不相信他会自尽,更不会相信他会偷窃他人东西,畏罪自杀,更不会荒唐地投汝河自尽。”
楚冬青摇头道:“他绝不会偷人东西的。”
“他死时,手中握着你们经丘书院的牙牌,是位郑氏子弟的,具体是谁,我便不知道了,正是这位郑公子,污蔑雨生偷了他的象牙玉牌,然后畏罪投河。
这漏洞百出的说辞,京兆尹居然听信了,并直接给雨生下了罪。
那可是投汝河,是诛满门的大罪,宣安城百姓谁人不知?
雨生就算想死,也断然不会投汝河,连累家人。
这明显是官官相护。”
楚冬青蹙眉呢喃道:“郑氏?郑珙之,又是他,难怪他昨天没来书院!”
“你认识他?”
“他与我是同窗。”
“你与他有仇?”
“不曾结仇,不过几年前,他曾对我下过黑手,那次正是雨生替我解的围,事后,雨生向我描述过对方的形容,其中有一人正是郑珙之。
但那已是陈年往事,当时我也忍气吞声了,并没有揭穿他的恶行,他没理由为此杀害雨生。”
“什么没理由,这就是理由。
恶人的心,天生就是黑的,而且越长越黑。
我打听过了,雨生虽然是溺死的,但身上有诸多伤痕,显然生前有被殴打过。
我一定要为雨生报仇!”顾当歌咬牙切齿道。
楚冬青劝道:“不要胡来,当务之急,是为雨生翻案,救出他妹妹。”
“怎么翻案?皇帝老儿久不临朝,早就不管事,这般蹊跷的命案,如此轻易便定罪了,这分明就是郑氏在从中作梗。
如今的朝廷是士大夫的朝廷,郑氏还是仅次于齐氏的名门望族,你要翻案,简直是痴人说梦。”顾当歌揶揄道。
楚冬青:“你杀了郑珙之,就能救雨生的妹妹了?”
“至少我能替雨生报仇!”
“报完仇之后,郑氏又岂会轻饶你?”
“这你放心,杀了郑珙之,我便带着老爹去北境,在那老子照样可以混得风生水起。”顾当歌不以为意道。
“那新麻衣客怎么办?”
“别跟我提新麻衣客,那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别翻案了,继续装聋作哑好了。”顾当歌不忿道,朝着楚冬青走来,路过其身旁时,停顿了一下,冷漠道:“麻衣郎君有你这样的胞弟,我真替他觉得丢人,感到羞耻。”
楚冬青杵在原地,沉默不语。
曙光破云而出,微亮微凉。
少年迎着光,一步一唱道:“肩道义,轻生死,见不平,血溅之,生人杰,死鬼雄。”
许久,楚冬青缓过神,猛地握住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气,额间虚汗暴出,两眼热泪盈眶而出,神情悲恸欲绝。
别人眼中,他楚冬青万事不上心,但却不知,凡是他为之上心的,皆是镂骨铭心。
此刻,他心如刀剐,痛苦万分。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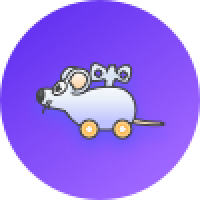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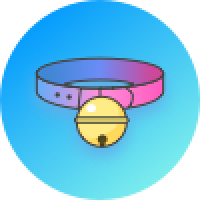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