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博士望着浑身湿透的,泪痕犹在的楚冬青,心生恻隐之余,不禁悔恨这些年的师德有缺。
他脱下外衫,披在楚冬青身上,温声道:“莫怕,先生替你做主。”
这一幕,委实惊愣了众人。
这还是那个整日为难楚冬青的谷博士?
就连楚冬青也是受宠若惊,很不适应。
谷博士朗声道:“好了,此事制止及时,先生便就此作罢,不再追究了,你们各自入座,准备授业了。”
郑珙之目光不善地望着楚冬青,挑衅之意,一览无余。
范征见状,暗骂道:“平日里瞧着颇有城府,不曾想是个蠢货,喜怒之间,忘形而不自知。”
楚冬青一改往日的孬样,目光没有躲闪,而是怒视回去。
鲁旦只觉得今天有意思,两个闷葫芦居然结仇了,谷博士好像吃错药。
意犹未尽的他,看热闹嫌事不够大,觉得必须添油炽薪,让这把火烧得更旺才行。
齐楼望着楚冬青的身影,神色自若,但心情大悦。
谷博士的授业时,依旧无聊乏味,时间一久,堂下学子便昏昏欲睡。
身为教书教书,必然有一套专治学生打瞌睡的法子。
谷博士的法子,便是跟读诗文,这明显很不高明,但他却一如既往的用着。
壬寅堂,书声琅琅响起。
楚冬青却一直心不在焉,他思绪纷飞,满脑子乱糟糟的,想的东西很多。
比如雨生究竟遭遇了什么,比如顾当歌是否真会对郑珙之下杀手,比如该怎么为雨生翻案,救他的妹妹,比如还能否为娘亲续命,还有谷博士为何会一改常态,是钟博士对他说了什么?
总之,越想心越乱,毫无头绪。
不知跟读了多久,谷博士突然停了下来,点名道:“楚冬青,你将这篇诗文背诵一遍。”
满堂学子皆是一惊,神色古怪地望着谷博士,难道那熟悉的一幕又发生了?
楚冬青茫然站起,披在身上的外衫,滑落不小心滑落了下来,他没有立刻将其拾起来,脑海中回荡着齐楼昨日说过的话。
谷博士看透了少年的心思,面带微笑道:“今日是先生在书院授业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先生教你们的最后一堂课,明日先生升任太史一职。
你尽管背,能背多少背多少,先生不会责怪于你。”
平日的楚冬青是可以背诵下来的,但今日心猿意马的他,只是囫囵跟读了几遍,印象模糊,根本没有把握背下来。
但是,他还是想尝试一下,每次他停顿下来,谷博士便是开口引导,最终断断续续地将那诗文给背诵了下来。
谷博士满心欣慰,不免自责道:“在为人师表这一方面,先生确实做的不够好,也罢,今后也就不误人子弟了。”
齐楼起身恭敬道:“先生,迷途知返,可喜可贺。”
谷博士摇头苦笑道:“托你的福,先生才能高迁。”
齐楼装无辜道:“学生可什么都没做。”
昨日一别,谷博士仿佛变了一个人,不似以前那般不苟言笑,此时眉眼间的笑意,显而易见,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在下堂之前,谷博士取回外衫时,在楚冬青耳边,轻声说道:“你以德报怨,委实令先生既感动又惭愧,先生就此向你道谢!”
楚冬青愣愣地望着谷博士,内心五味杂陈。
临走之前,谷博士望着诸学子,最后只撂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了。
“你们要好生念书,这世间读书郎,应如天上星。”
这句话,但凡蒙学过的人,便听过,只不过在晏国,真将其当一回事的人,却很少。
道教求长生,佛教求轮回,儒教求天理。
儒教书生的修行,与道佛两教不同,讲究的是修心,至天理。
修儒是很鸡肋的一门修行,因为他们生前,若只是修儒道,那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除了满嘴的大道理外,便无任何过人的本事。
但儒修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他们在死后,其神灵会如昙花一现重回人世,且具有一定神通。
所以,世人是这般评价儒修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在晏国,读书人虽不少,但最终真正算得上儒修的,却是凤麟毛角,因为晏国对儒修一事,至今还只是了解点皮毛而已。
谷博士一走,有人便等不及要发难,他直奔楚冬青的书案前,居高临下,理直气壮道:“世胄子弟讲究颜面,你平白打了我三拳,这笔账得算,我也不欺负人,你打了几拳,我便还你几拳。”
楚冬青站起身,凭借身高的优势,垂眼望向郑珙之,认真说道:“欠下的总得要还,这三拳我还你,雨生的命,我也会血债血还。”
郑珙之只想践踏楚冬青,来彰显自己的威风,一博众人的眼球,但他没想到,这次一脚踢在了铁板上,楚冬青在那位少年的死上,不再软弱可欺。
更可怕的,楚冬青还一口咬定了他就是凶手。
这一切,皆令他很不爽。
他嗔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凶手,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否者信口开河的污蔑世胄子弟,我就算打死你,也不过分。”
齐楼看不惯,不咸不淡地说道:“庶族污蔑士族,死有余辜,但这个穿麻衣,可不是庶族百姓,他是大司空之子,且是唯一的血脉,打死他,你一个郑氏非嫡出的子嗣,恐怕一死也难抵命。”
鲁旦一脸震惊地望向齐楼,疑惑地问道:“表兄,有这么严重?”
“以前岭北是八大士族,以后便是九大士族了,楚氏虽穷,但晏国的声望,将是首屈一指。”齐楼毫不夸张地说道。
范征不知何时来到郑珙之的身旁,拍了拍肩膀,脸笑皮不笑地说道道:“就此算了吧!”
“可是......”
郑珙之话还没说完,整个人便飞了出去,并一连撞翻数人。
范征收回拳,甩了甩衣袖,面笼寒霜地望着郑珙之,毫不忌讳地说道:“为你这种蠢货擦屁股,是我至今为止干过最愚蠢的一件事。”
此话一出,满座愕然。
楚冬青一把抓住范征的手臂,问道:“你知道些什么?”
“有趣!”齐楼笑道。
鲁旦戏谑道:“不愧是金刀士的头,这种烂屁股你也敢擦,不嫌臭吗?”
范征笑了笑,若无其事地说道:“入我金刀士,我范征便视其为手足。”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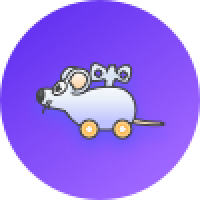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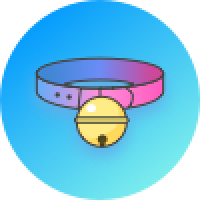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