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冬青熬好了药,端至娘亲的床榻前,温声道:“娘亲,该喝药了!”
苏寓娘憔悴一笑,虚弱道:“虎头,药太烫了,等凉点再喝!”
“药凉了,喝起来就更苦。”
“无妨,娘不怕苦,你给娘说说,今天你在书院都发生了些什么?”
苏寓娘卧病在床,极少出门,对外面之事,一概不知,每日儿子散学后,喂她喝药时,便会要儿子讲一些身边的所见所闻给她听,权当解解闷。
楚冬青沉吟了半响,不知如何开口。
知子莫若母!
苏寓娘叹息道:“今日你回来,娘亲见你神情沉重,便知我儿有心事!”
楚冬青天性耿直,悲喜形于色,哪怕刻意隐瞒,善于察言观色,或者熟知他的人多少能瞧出些端倪,又如何能瞒住他的娘亲呢。
楚冬青面露悲戚,沉声道:“雨生死了!”
“怎么会?”苏寓娘惊愕道,这些年,他没少从儿子的口中,听闻雨生的事,此刻得知其死讯,不由悲从中来。
楚冬青将雨生的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娘亲。
苏寓娘听完,愣怔得久久说不出话。
她很后悔知晓此事,所以她试图佯装不知情,呢喃道:“娘亲有些困乏了,喂我喝药,喝完药,娘亲要休息了。”
楚冬青凝视着娘亲,一脸认真地说道:“娘亲,药还没凉!”
苏寓娘神色慌张,目光有意躲闪,不敢儿子正视,连连摆手道:“无妨,无妨,娘亲不怕烫!”
“娘亲!”楚冬青郑重其事地喊道。
苏寓娘没有多少气色的脸,愈发苍白,她瘫靠在床榻上,低声道:“虎头,娘昨日给你说过的话,你就给忘了吗?
这宣安城不缺行侠仗义之人,为什么就非得是我儿呢!”
“为什么就不能是孩儿呢?”楚冬青反问道,并据理力争道:“雨生的案子,很棘手,他人或许有心为雨生翻案,但成事艰难,远胜于孩儿。
雨生的在天之灵,应该也更希望为他翻案的那个人是孩儿。”
苏寓娘哀声道:“虎头,娘只剩你一个儿子了!”
“娘,孩儿已经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痴儿了。
因为愚笨,孩儿打记事时,便处处受人嘲笑与冷眼,但孩儿从不曾向娘亲说过一句怨言。
但是时至今日,孩儿得知雨生的死,才明白过来,在这世间哪有什么独善其身,当恶人挥刀砍来时,不是跪地求饶,就可以平安无事的。
雨生曾告诉孩儿,虽然他如沟渠一般,但他心中也藏有一轮明月。
孩儿何尝心中没有一轮明月呢?
苟活于世,当砧板鱼肉,任人宰割,并非孩儿所愿。
孩儿也想如父兄一般,为这世间之人,尽一份绵薄之力,当个受人尊崇的人。
不瞒娘亲,孩儿已经拜钟先生为师,成为太玄宫弟子了,而且明日孩儿便去京兆府击鼓鸣冤,替雨生翻案。”
苏寓娘见儿子潸然泪下,也跟着泪如雨下,泣声道:“我儿有此志向,为娘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罢了,罢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这当娘的,自今日起,每日为你祈福,求上苍保我儿平安。
虎头,但你要切记,行侠仗义,惩奸除恶,切不可如你阿兄那般意气用事,替天行道,不到万不得已,莫要伤人性命,恶人交由官府惩处就好了。”
楚冬青点头应道:“孩儿谨记娘亲之言。”
郑氏府邸,郑珙之此时正跪在堂屋,此间还端坐着不少郑氏主事之人,连郑氏当代家主郑康,也正坐于高堂上,不过他的老脸阴沉至极,而其他人也脸色很难看。
郑康陡然拿起桌上的茶杯,狠狠地砸在郑珙之的脑门上,并一掌拍烂桌面,他寒声道:“安儿,虽说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但是为了郑氏,你要懂得取舍。”
郑珙之的父亲郑安沉声道:“爹,你放心,若是真到了那一步,侄儿不会让你失望的。”
“权儿,你作为兄长,且有四个儿子,前些日子你那小妾又生了个大胖小子,若真到了那一步,你便将那幼子过继于安儿。”
郑权不满道:“爹,四弟还年轻,努努力,将来肯定还可以生,我那幼子在......”
郑康未等他将话说完,恨铁不成钢的大声呵斥道:“说过多少遍了,家族团结和睦,方可久兴,你连一个介子都舍不得,将来如何掌管偌大的郑氏。”
郑权唯唯诺诺道:“爹教训的是!”
郑安打圆场道:“爹莫动气,那楚家二郎庸人之质,掀不起什么大浪,为了防患于未然,今夜孩儿便亲自去解决掉那个做假证的。”
“这种事何必四弟亲自动手,该是家中门客出力之时了,否者豢养他们的意义何在?”郑权献策道。
郑康气得吹胡子瞪脸,对长子的不满,一览无余,不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也就罢了,在关乎家族存亡之事上,居然想着偷懒,托付于门客手中。
一想到将来家主之位,要传于长子,他更是痛心疾首。
郑权拜谢道:“大兄有心替小弟着想,但此事容不得马虎,唯有小弟亲力亲为,方可放心。”
“就此而已?”郑康问道。
郑安冷漠地望向头破血流的儿子,寒声道:“即日起,你禁足在家,哪里也不许去,书院也不用去。”
郑珙之神色恐惧,哑然点头,他不傻,明白禁足意味着什么,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他爹会为了家族,还不犹豫地杀掉自己,毕竟从小到大,这个男人都不曾对他唯一的亲生骨肉,表现过哪怕半点儿关心。
郑康很是喜欢幼子,不管是于兄于弟,他皆敬爱有加,为人办事牢靠,懂得取舍,又能顾全大局,这才是继承家主的不二之选,奈何家主之位,向来只传嫡长子。
忠字桥金善坊的鸿运赌坊中,一位脸上长着一颗大黑痣的瘦汉,输得两眼赤红,他昧着良心做假证,赚来的三十两银子,不曾想一天就输个精光。
月黑风高,刘二狗垂头丧气地出了赌坊,身为打更人,提着灯笼,向来不怕走夜路的他,因做了亏心事,一路上提心吊胆,念念叨叨地嘀咕:“冤有头,债有主,杀你的人不是我,我也不想做假证,但不做,我就得死。”
归家途中,要经过好一个偏僻的长巷,当他走到半道时,一阵阴风吹过,灯笼里的火光,离奇地熄灭了。
他吓得脊背发凉,摸上腰间的铜锣,一个劲地猛敲,惊魂未定地慌跑着。
钩月如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巷中,一柄长刀出鞘,光洁如霜的刀身,借着月光微微,却是那般的夺目。
刘二狗见状,当即止步,吓得瘫软在地,一股尿骚味从他裆下弥漫出来。
黑衣人二话不说,执刀朝刘二狗奔杀而来。
刘二狗满目绝望,在求生欲的驱使下,连滚带爬,反身欲逃。
但黑衣人步伐之快,岂会容他这腿软之人逃脱?
转眼间,二人相距不过数丈,黑衣人纵身跃起,刀光先冷刃一步,落于刘二狗的脖子上,眼见就要鲜血飞溅时。
三颗飞石衔接而至,快如流星,袭向黑衣人要害。
黑衣人惊觉,反手挥刀抵挡,接连击飞两枚飞石,自知来不及弹开第三枚飞石,只能扭身躲避,虽然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要害,仍旧击中了他的胸膛。
小小一粒飞石,却势大力沉。
黑衣人闷哼一声,一口逆血从喉咙口涌出,他惊骇道:“是何高人?”
那人没有现身,语气很平淡地说道:“你不是我对手,这个人你杀不了。”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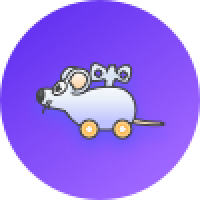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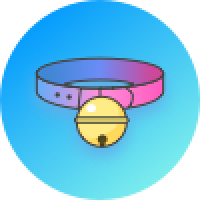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