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的冬风吹袭着,整个平洲万物衰败,一派萧条。偶尔的炎阳天气从寒冬的包裹中挣脱出来,可温暖的时光却总是短暂,大风吹散了阳气,吹的凌风城上的旌旗猎猎作响。
时间来到永风历元年冬至夜,正是凌风国开国改元的第一年,而冬至是平洲人的年庆,整个凌风城都沐浴在喜庆之中,寒冷没有驱散国民的热情,战争的阴霾,并没有蔓延到这里,王宫中的告天台上,风王凌天和他的将军墨征在这里对弈。
墨征穿了一件宽松的黑袍,大半拖沓在地。这种夸张的官服在王宫中随处可见。越大的官,越需要更大的气派,而官服,很直观的体现这一点。
“您已输了三局,我的王,难道您还要再下?”
凌天凝神审视着棋局,寻找着起死回生的可能,可黑子错落有致,白子已然覆灭,落子之精妙看得他连连点头,已经忘记了寻找生的可能,反而夸起了对手的棋艺。
“每输一局,都让本王明白一个道理,再来!今晚就让本王输个醍醐灌顶。”凌天笑着说道,上唇两撇胡子舒展开来,如同两条眉毛。
“棋局好比战场,风王赢战争无数,但您知道什么下棋总输给我吗?”
“第四局还没开始,现在说输赢为时还早,这局我一定赢你。”风王笑着说,语气中透出毋庸置疑的乐观和自信,就跟他在战场上对阵前鼓舞士气的话一样。因为他总是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墨征回应一个神秘的笑容,“看来得下完第四局,王才愿意听我讲为什么总是您输了。”
两人麻利的将黑白子拾入木盒,准备第四局对弈。
“此前平洲民不聊生,我起兵肃正,终平天下。”风王说。
“有句古话叫‘天发杀机,斗转星移;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战争伤害的终究是平洲万民呀。”
“我也有句古话,叫‘祸兮福所倚’,治乱世不能不战,这就叫祸中求福。”
“可是害生于恩,但愿平洲从此不要再战。”墨征说着,落下一子,扼住了白子咽喉。
凌天跟着落下一子,说道:“南窜逆贼,号称兄弟会,在民间作祟,过完年庆,本王便御驾亲征,剿灭他们。”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王还是少做杀孽,小心了!”墨征说着并使了一个眼神。
“先贤说过,‘攻其地,爱其民,攻之可也;杀逆贼,安顺人,杀之可也’。你为什么反对我出征呢?”凌天不以为意,皱着眉头问道。
“风王奉天承运,一统平洲,眼下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这个时候再燃起战火,臣下以为不是时候。”
“我这是以战止战,等剿灭兄弟会余孽,平洲不是永世和平吗?”风王高谈阔论,语腔放大,似乎南征已然胜券在握。
墨征没有说话,而是重重的扣下一子,凌天眉头一皱,迟疑了一会,
“大势已去!”他不由得感概一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你又输了。”
“墨征呀墨征,好了,你说说我为什么会输。”
“恕臣下斗胆谏言。”
“少来这套,别磨叽!”
“王的棋观,只看重这一横一竖的得失,王的天下观,过于看中疆域的宽广。”
风王起身,将视线从棋盘上移开,面色腻重的看着墨征:“继续说。”
墨征起身行礼,“我的棋观,不再横竖,而在于心,故既知敌,就能破敌;臣下认为天下的观有三,一是疆域,二是民心,三是政道。”
“你是觉得本王只看重疆域,不问民心?”
“微臣不敢,只是战事再起,祸及平洲万民。”
“那你的意思是逆贼也不打了?”
“要打,但是要发仁义之师。风王既然已经坐上王位,应当奉天领命,以仁治国,这样才能民心所向,王国巩固。”
“听君一言,茅塞顿开。”
墨征转头,远眺凌风城,夜色下的凌风城也是极美,特别这年庆时节,横竖的街道上点缀了星星之火,凌风城的灯火阑珊和夜色中的璀璨星辰交相辉映。
“凌风城民心安定,城池高筑,南方小患不足为虑,东北高地人兵强马壮,虎视平洲,不得不防。”
“哈哈……本王也有此意!”风王凌天朗声大笑,走向告天台前,使出浑身劲数宣布:“令!封墨征为卫戍侯,镇守东北大关;令!筑工府筹集资财,勘察地形,外城筑墙,御敌于国门之外!”
……
平洲南部,大陆边缘。
一个寂寥的身影在芦苇丛中穿梭,枯黄的手遮挡着太阳,隔着韦叶不断的眺望,他想看看江水退去了多远,自己还能砍多少芦苇,而不用浸在那该死的刺骨的冷水中,他用另只一手随随意拭去渗在额间皱纹里的的汗水,然后用他那枯黄的手揪起一把芦苇,另一只手朝着芦苇根部狠狠砍剁下去,却没能一刀斩断。
几声隐约的哭声从芦苇深处传来,老头竖起了耳朵,潜心的静听了一会儿,那是芦苇深处传来的哭声。他手脚并用的拨开芦苇,向芦苇荡的深处探查,声音愈加清晰,分明是两个孩子的哭声,任凭锋利的苇叶划破老头脸上和手上的老皮,他反而走得跟快了。
这是一只精致的深槽木桶,刷着富贵人家特有的朱红漆色,桶边还镶着金色的花边。木桶内两个孩童正嚎啕大哭。
“可怜的孩子。”他望向北面,那里的天色十分阴沉,“战火起,富贵和贫穷的都要遭殃!”老人心中喃喃道,随后一手一个娴熟的抱起孩子。
将一小捆芦苇背于肩上,砍刀悬于腰间,老人头顶着朱红色的镶金木桶,颤颤悠悠的往家走去。心里想到:“这金丝木桶应该能去市集换些钱财,抚养这两个小可怜长大。”
天近黄昏,午后那温暖和煦的光线,现在已经逐渐转变成阴冷的淡蓝色,起风了,枯叶旋转着随风扬起,又散布于整个老人的视野中,一幢简单的木屋处于视野的中间,依靠着山体,墙体是用圆木排列而成的,缝隙里塞满了枯黄的芦苇叶,屋前围了一方院子,芦杆做的篱笆在风中摇曳,随时可能会被风带走。
“孩子们,爷爷回来了。”
闻声出迎的是几个十来岁的孩子,黝黑粗糙的皮肤,一边笑着帮老者卸芦苇,一边帮着抬木桶。几个孩子都有些好奇的望着精致的木桶,黑色眼睛滴溜溜直转。
“孩子们,你们又有新的弟弟和妹妹了。”老人带众人进屋。“唉,战事不停,万一老朽走了这帮小可怜可怎么办?”老人嘴巴喃喃,专注的用烧红的铁丝在两个孩子的肩上轻轻地烙下了“拾陆”“拾柒”两个字样。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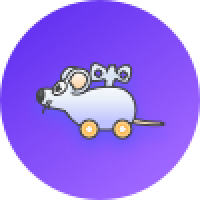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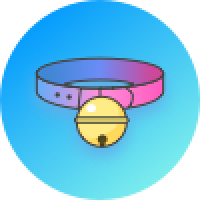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