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音大小礼堂进行声乐摸底考,观众席坐满凑热闹的音乐系新生。
同学们在台下交头接耳,丝毫不在意舞台上是不是有人在表演。
音大的每个学生都骄傲地认为,只有多才多艺的自己才是下一个明星。
希冀就读在通俗音乐学院,主修流行音乐演唱。
这时候,她站在小礼堂的舞台上,放下麦克风,
路过专业老师老李,他的手里拿着名册,用“到时间吃午饭了啊”的口气,问:“希冀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写歌的啊?”
希冀想了想,“大概七八岁,怎么了老师?”
“没什么,很好。”老李继续看向演台,“挺好的。”
在希冀的印象里,李老师向来孤高自傲,自打过完五十岁生日,言谈举止就开始走深沉路线。虽然希冀不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当自己唱歌时,至少有一个人在用心听,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下节是表演课。
希冀和莓莓走出小礼堂,去隔壁班去推上课要用的道具车。
大学里在盖教学楼,体育馆在翻新,足球场在重建,宿舍也拆迁了。
音大可真有钱。
不断飘过的云朵遮住太阳,露出一浅钩儿灼烈的白光。
希冀用手掌遮住太阳,仰起头看天。
于是白皙的脖颈完全曝露在衣领外。
或许,有人会看见北斗星。
“等一等,希冀,脖子露出来了!”
院楼台阶下,莓莓扯住希冀胳膊,整了整她的衣领,像家庭主妇一样唠叨不休:“希冀,这种天气穿高领衣服,不舒服吧?但,还是遮住些比较好,学校里这么多人,你知道,有些家伙就喜欢在背后乱嚼人是非。”
希冀笑了笑,“没事的,我还给它们取了名字呢,天枢、天璇、天权……”
不厌其烦地一颗一颗数着“她的星星”。
希冀的星星,和天上的星星不一样。
如果说闪烁的星是钻石,划过的星是眼泪,那么“希冀的星星”便是画家甩在画板上的油料,作家滴在纸上的墨水。
七颗胎痣。
从锁骨至颈边,往蝴蝶骨延伸。
莓莓推着道具车,“取了北斗七星的名字吗,白娘娘的儿子是文曲星,难道你是什么星下凡来着,不会也是霸星吧?”
希冀淡淡笑着没回应。
她发现莓莓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并不像以前那么尴尬了,但却仍然处处警惕,时时提醒,让希冀将自己的缺点掩藏起来。
莓莓,全名苏莓,希冀的同寝姐妹。
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女生们在班级里自我介绍,希冀环视着四周异样的眼神,然后侧头露出脖子,给女生们看她的胎痣。
女生们笑着说“好有个性啊”。
只有苏莓不一样,她像一个被人看出修坏了眉的女孩,摘掉自己丝巾,勒住了希冀的脖子,毫不委婉地说:
“希冀,咱学的是音乐表演,将来要当艺人的,不要把缺陷露在外面,我的天,整整七颗啊,将来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做掉,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侬晓得伐?”
当然晓得啊。
她跟它们朝夕相处整整十八年呢。
七颗胎痣。
按照北斗七星的顺序依次杓形排列,色泽美艳浅粉。
希冀还晓得,这么多数目的胎痣盘踞在颈项,任谁都会觉得触目惊心吧?
小时候她以为,七颗胎痣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褪去。
可是,小家伙们太坚强。
一年一年越发地执著了,宛如夜空的北斗星那么亘久不变。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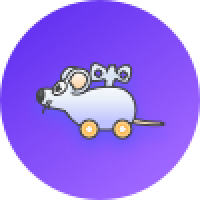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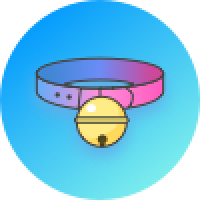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