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的地平线露出了半个金红的太阳,阳光已经把大地照的微微透亮。马重阳和白衣书生缓缓走出树林,此时,二人感到身心疲惫,也许这一晚,对于这两个十五六岁少年来说,是一次平生难忘的经历。
“喂,我说马重阳,昨天在明月楼,我让你离开,你怎么又回来了呢?难道不要命了?”
马重阳听后顿时一愣,自寻思道:“原来我身后的二指宽的布条是这韩公子所留,可这韩公子是如何知道官兵会来明月楼抓人的呢?难道是这位韩公子向官府通风报信,引来的官兵?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还要出手相救于我和那说书老者呢?”一时之间,马重阳的脑海里满是疑团。
白衣书生见马重阳发愣,没有回答,便上前一步,轻轻的在马重阳的面前挥了挥手道:“喂,喂,重阳兄!”
马重阳忽听得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才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原来是这样,不过……”
白衣书生见马重阳说话吞吞吐吐,只说了半句话。心中不解,寻思,难道重阳兄心中忌惮与我?不能啊,我与重阳兄虽然接触时日不多,但觉他是个好爽侠义之人,我又救了他的性命,难道这重阳兄瞧出了什么吗?或许是我多心了,不如问他一问,自然知晓,于是上前问道:“不过?不过什么?”
“不过……”马重阳语气略有迟疑。
“你这人,有话便要直说,怎么婆婆妈妈的!”
“不过,你是如何知道官兵要来明月楼抓人的呢?难道……”
“难道什么?重阳兄该不会是怀疑我是那通风报信之人吧?”
“我只是想不明白而已”
白衣书生听后,大笑道:“这么大的明月楼,居然没有店小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确实奇怪,这店小二呢?”马重阳疑惑的问道。
“这个明月楼原本是有个店小二的,在角落里,面容冷漠的盯着这说书人,他的眼神让我起了疑心,便暗中观察他,忽然发现,在说书人来了之后不久,便从后门溜了出去,这举动让我感更加到奇怪,正门不走,反走后门,一定有可疑之处,便暗中跟随与他,竟然发现他去官府通风报信,我想若是官兵来了,这说书人必定惹上麻烦,于是便回了明月楼准备搭救这说书老者。”
“可你为什么又要提前告知与我,让我离开呢?”
白衣书生嫣然一笑,反问道:“,你又为什么要出手相救这说书老者呢?”
马重阳见白衣书生这样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寻思了片刻,才朗声回道:“大丈夫见人处于危难之中,岂有不救之理!”
白衣书生瞧了马重阳一眼,见马重阳表情严肃,语气坚决,卟哧一笑,道:“不怕死?”
“怕,就不会死吗?”
“不怕,就不会死!”
“大丈夫,生何所畏,死又何所惧!”
……
二人边走边聊,甚是投机,路边良田几亩,却只有几个老弱妇孺在田间吃力的挥动锄头耕种。这田间耕地本应该是壮硕男子干的活,如今怎么会是几个老弱妇孺在田间劳作,二人感到很是奇怪。
“这位大婶,你家男人怎么不来这田里干活啊?”马重阳心中疑惑,便走上前去问道。
几个田间劳作的妇人互相对望了一眼,有的苦笑,有的叹气。其中一个中年妇女把锄头一端插在地里,扶着锄头另一端,用衣服的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长叹道:“哎,那还有什么男人啊,家里的男人都被抓去当了壮丁,留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的,没办法,这地要是不种,来年就交不起官府收的赋税,饿肚子倒是小事,可以讨饭为生,若是不交税,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可就不保了!”说着,泪水在眼圈中打转。另一个妇人,也停下手中的农活,说道:“哎,我们有地可以种,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如果哪天官兵来了,把这水田改成牧田,那我们这一家老小的,来年又要挨饿了!”说完,抬头瞧了一眼天上的烈日,见被乌云已经遮蔽,便摇了摇头,长叹一声,拿起锄头继续在田间干活。
马重阳听后,感到心中很是酸楚,吟诵道:“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白衣书生听到马重阳吟诵杜甫《兵车行》中的一段诗句,心里不由得也是感触良多,他瞧了一眼马重阳,见他眼圈发红,喉咙哽咽,随即掏出一锭银子,递给了这位大婶,那大婶接过银子,不停的作揖道谢,白衣书生只是微微一笑。
“韩兄,即便你给她银子,也只是解决她一时之苦,却不能了去她心中之苦啊!”
“你我人薄言轻,又能如何呢,眼下也只能做到如此了!”
“哎,韩兄言之有理啊!”
随后二人继续赶路,不一会的功夫,二人便回到了城中,他们走到城门下,发现前面不远处围拢了一伙人。
“重阳兄,不如我们走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马重阳点了点头说道:“也好”
于是他两个人便挤到人群中,只见几个恶奴围着一个老者和一女子,拉拉扯扯的,嘴里还骂骂咧咧。看样子这一老一少,是父女二人,这群恶奴呢,看似是要把这少女抢走的架势。仔细观瞧这女子年龄约十三四岁上下,长得眉清目秀到有几分的姿色,但见得,一恶奴眯着眼睛,抢身过去,当即一把抱住这女子,揽在肩上,哈哈大笑道:“小娘们儿,今晚陪大爷们乐呵乐呵!”。这女子拳打脚踢,拼命挣脱,誓死不从。
另一个恶奴斜眼瞧了一眼这老汉说道:“我说老头,我们大哥,看上你家闺女,这是你们家的福分,劝劝你闺女,从了我大哥,即刻便跟我们回府,享受荣华富贵!”
“这位老爷,你行行好吧,我这闺女还未曾许配过人家啊!她年龄还小,不能跟你们回去啊!”这老汉不停的作揖,说好话。只求得这帮歹人能放过自己和女儿。
这恶奴把眼一瞪,恶狠狠的说道:“不肯?我说老头,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
那老汉当即抱住这恶奴的一条腿,说道:“求求你,放了我家闺女吧!”
这恶奴见这老者抱住自己的一条腿,行动十分不便,怒骂道:“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兄弟们动手”说罢,抬腿就是一脚,正正的踢在老汉的胸口,这老汉捂着胸口,连退了几步,踉踉跄跄,终究站立不稳,闷声摔倒在地。这七八个恶奴,顺势一拥而上,将老汉围在当中,你一脚,我一脚,把老汉踢得在地上叫苦不迭,身体蜷作一团。
一旁的女儿,哭的是死去活来,虽然被人揽在肩上,但依旧拼命挣脱。只见,这女子在恶奴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疼的这恶奴大叫“妈呀!”一声,松开了手臂,将女子摔倒在地,这女子赶忙起身,扑到老汉身前,用弱小的身躯护住老者,泣不成声的说道:“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一个恶奴捂着手腕,嘴里大骂道:“小娘们儿,居然敢咬老子,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另一个恶奴骂道:“你这废物,连个小娘们儿都看不好!”
另几个恶奴见此情景,互相对望了一眼,收起拳脚,一个子略高的恶奴猥琐的说道:“不,不打也成,你得跟我们回,回去,让,让我们哥几个乐呵乐呵”说着,伸手就要拉扯女子的手腕。
此时正在一旁围观的马重阳和白衣书生早已经看出,这哪里是说婚,这分明是强抢民女的一伙歹人。马重阳怒火中烧,双拳捏的咯吱作响,二目圆瞪,再也按耐不住了,抢身就想从人群中冲出去。但却被白衣书生一把拉住衣襟,说道:“马兄,看我的!”话音未落,白衣书生一个箭步跳到几个恶奴近前,用手指牢牢的掐住一个恶奴的手腕,一用力,这恶奴的手腕好似被铁环锁住一般,疼的是呲牙咧嘴,赶忙回身骂道:“他娘的,谁,谁啊?松手松手!”只见这白衣书生面如冰霜,手指顺势向外一用力,只听“咔擦”一声,这恶奴的胳膊被折断了。恶奴惨叫一声,疼的这恶奴脸色惨白,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清晰可见。
白衣书生一只脚踩在这恶奴的脊背,另一只脚用力猛的踹向这恶奴的膝盖,只见这恶奴一个踉跄,顺势跪在地上。白衣书生高声呵斥道:“你们是谁家的狗奴才,竟然敢强抢民女,仗势欺人,我问你们,这父女既然不肯,为何要逼迫人家!”
其他的几个恶奴都被吓的傻了,哪里还听得到白衣书生的问话。他们各个双腿发软,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嘴里还嘟囔着:“好汉饶命,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不敢了?那可不行,小爷我最恨的就是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即便做了之后呢,又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也就罢了,还不肯承认,你说这样的的人,可不可恨?”
几个恶奴听后又点头,又是摇头。
“哎呦,糟糕,真是不巧啊,你们今天运气差了点,赶上小爷我今天心情不好,这可怎么办?要不今天就索性饶了你们?若是就这样放过你们,我连自己都说不过去,我自己怎能骗我自己,既然如此,不如,你们一人留下一只耳朵,让我对自己也好有个交代!”话音刚落,白衣书生随手掏出一把匕首,丢到这几个恶奴的近前。这几个恶奴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吓的魂飞魄散,有的裤裆都被吓尿了,急忙磕头如捣蒜一般。
“怎么,难道还让小爷我亲自动手不成?”
白衣书生手起刀落,只听一声惨叫,一个恶奴的耳朵,已经血淋淋的被割下。眨眼间,又是几声惨叫,地上又多了几只耳朵,这帮恶奴疼的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都给我滚。狗奴才,谁愿意看你们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快滚!”
几个恶奴见这白衣书生不杀他们,一个个捂着耳朵,赶忙起身,撒腿就跑,不一会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父女二人都被眼前的一幕吓的呆住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又是作揖,又是道谢。白衣书生赶忙扶起父女二人说道:“赶紧离开这里,免得他们回来报复!”见父女二人逐渐走远,回身双手抱拳对马重阳说:“重阳兄,你我很是投缘,但我还有要事在身,等我办完事还会来找你的,咱们就此别过吧!”
马重阳凝望着白衣书生的背影在人群中逐渐消失,心中有些不舍,于是又高声喊道:“韩兄,路上小心,咱们后会有期!”
过了好一会,马重阳才收回目光,不在凝望。他向城里走去,走着走着,猛然间,闻到阵阵酒香扑鼻。这酒怎么这么香,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于是,他心生一念,大步的向酒楼走去......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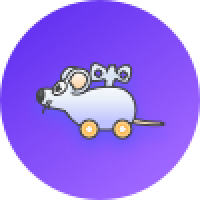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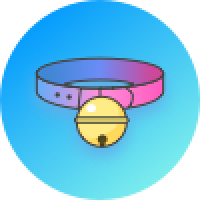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