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的太阳被西边的地平线渐渐地淹没,一轮金色的,又圆,又大,又亮的月,却缓缓的从东边升起。夜,就这样悄然而至,吞噬了最后一缕阳光。马重阳骑在马背上,昏昏欲睡,他早已无心欣赏坠在繁星中,这金色的又圆,又大,又亮的月,此时的马重阳唯一能让他动心的只有食物,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这种饥饿感,仿佛是一团烈火腹中灼烧,让他直不起身来,蔓延到全身,瘫软无力。在马重阳的眼中,夜空中的这轮又圆,又大,又亮的金色月亮,仿佛就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煎饼,如此诱人。
可惜月亮就是月亮,怎么可能变成煎饼,就像理想和现实永远是遥不可及一样。就在马重阳似睡非睡,半昏半醒的时候,马重阳的骑得这匹枣红马却突然停住了,不往前走半步,正正的停在一条溪水边。马重阳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没做半点防范,乎的一下跌落马下,人有的时候总会在危机关头,做出乎常人,意想不到的本能反应,这就是人的潜在机能。马重阳也不例外,就在马重阳的身体离地面还有一尺高的时候,马重阳本能的双手一撑地面,身体向前一纵,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后,稳稳的站住了。马重阳向前走了几步,飞身一跃上马,轮起马鞭,在马背上狠狠地抽了几下,这枣红马闷哼了几声,马蹄却纹丝不动,马重阳感到很是奇怪,跃身下马,拉住马的缰绳,用力的向前拖拽,只见,这枣红马嘴角已被这缰绳勒出鲜血,马蹄却依然未动半步。马重阳见此状,怒声喝道:“好你个牲畜,难道此刻你要为难我马重阳不成?”说罢,狠狠地将马鞭摔在地上,仰头望天,只见星辰闪烁,明月高挂。再瞧这匹枣红马,一扬马头,抖了几下,迈开长蹄,缓步向溪边走去。马重阳这才明白,原来这匹马是又渴又饿,不禁的自语道:“人又如此,兽何以堪啊!”。过了片刻,待这枣红马饮饱了水,马重阳无意间,向前方望了一眼,只见溪水对岸,隐约有灯火之光。马重阳大喜,哪里还顾得上腹中饥饿之事,纵身上马,向溪水对岸飞奔而去。
马重阳穿过潺潺溪水,纵马大约行至二三里路,过了半碗茶的功夫,这才瞧得原来这光亮,是一家客栈杆子上挂这的灯笼,马重阳纵马走近抬眼观瞧,这血红色的灯笼在黑夜中,格外的通亮,在风中左右摇曳,但上面“溪水客栈”四个大字却清晰可辨。马重阳跃身下马,疾走几步,轻轻推开木质的大门,抬眼朝屋内望去,这客栈,一眼瞧去与平常的吃饭,住宿的客栈别无两样,土坯的屋墙,二层格局,几张木制的座椅板凳摆放的规规矩矩,桌子上的几栈油灯昏昏暗暗,却把屋内的情景照得一清二楚。摆设虽然略显简陋了些,但倒也干净。
“呦,我说这位爷,站在门口瞧什么呢?既然来了,那就里面请吧!”
马重阳被这柔声一震,只觉得身上骨酸肉麻,甚是不自在,随声音瞧去,只见,一女子,这女子与马重阳平日里见过的女子却大不相同,长长乌黑的秀发随意盘起,插在秀发上的却不是平日里女子常用的发簪,而是一根普普通通的筷子,对,就是平日里吃饭用的筷子。她一只脚豪爽地跨在长凳上,纤纤长指反复玩弄着垂下的一绺秀发。身穿朴素的长纱衫,却难以遮掩将弹指可破的肌肤,昏暗的油灯下衬得更加湛白。
“喂,我说这位爷,您是住店呐,还是打间啊?要是看上别的,您也大可以随便说!”说罢,暧昧的向马重阳一笑,这笑容如此的勾人魂魄,让人难以抗拒。随即,这女子提着一壶茶水纤腰微步,缓缓向马重阳走来。一阵阵幽香扑鼻,在灯光映照之下,这女子容色晶莹如玉,即便脸上未施粉黛,绝色娇容却难以遮掩,如此清新动人,如新月生晕,如花树堆雪,娇柔婉转之际,美艳不可方物。她双眸微眯,刻意的回避众人的目光,让你看不透眼睛的明澈,眉宇间流露出的冷峻杀气,即便是娇媚之美也无法掩饰。佳人归是佳人,但不由的会让人心生一股冷艳和畏惧之感。可马重阳却好似什么也没看到,弹了弹身上的尘土,大步走到一张靠边的位置坐了下来,道:“在下是要住店,不知老板娘这里可有吃喝?”
那女子从衣襟里套出一张丝质的手绢来,搁到了嘴边,柔柔的笑了几声之后,回道:“我这店做的就是住宿,吃饭的买卖,虽说地方偏僻了点,但您也不问问这过往商旅客人,哪个不知道老娘我开的溪水客栈!”
“既然如此,那就来一壶好酒,几个下酒的小菜便是!”说罢,马重阳拎起桌子上的茶壶,自斟了一碗茶,饮了起来,此时的马重阳已经无心在欣赏这老板娘的妩媚和娇柔之美,在他看来,填饱肚子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你们傻站着看什么?还不赶紧给老娘干活去,养了你们这帮死人!”说罢,这女子抓起桌子上的一块抹布,“啪”的一声,不偏不倚的丢在店小二的脸上,一道血红的印记,那店小二捂着脸冲这女子“嘿嘿”一笑,眨眼间窜到后厨去了。
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一壶老酒,几盘小菜和几个热气腾腾的白馒头都已经备好,马重阳抬手,抓起一个热气腾腾的白馒头,也顾不上烫手了,整个塞进口中,还没来得及咀嚼出滋味,就囫囵的吞了下去,随后,又塞了几块酱牛肉,大口的咀嚼起来。他真的饿了,眨眼之间,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
就在此时,只听得,门外人厮马蹄吵杂之声,声音由远渐近,片刻后,一队人马,吵吵嚷嚷的推门而入。
“呦,又来了几位爷,小六子,赶紧招呼客人,老娘我怎么样了你们这帮不抬眼的废物!”这女子怒道。
马重阳随声撇眼瞧去,此刻才注意到这一行人等,大约有十几个年青壮硕之人,前面为首一人,年纪约四十岁左右,身穿黄色道袍,大帽下却瞧不清楚容貌,黑布包裹的长剑背于身后,而后面的则是几个人状汉,赤膊上身,身上的肌肉青筋暴跳,依然可辨。抬着一口硕大的油漆棺材,想必这棺材倒是崭新的,连油漆都是刚刚涂上去的。马重阳打量了半晌,方才心中惊愕:“这为首的一人不是崆峒派的弟子吗?这崆峒派的弟子怎么会在这溪水客栈出现?”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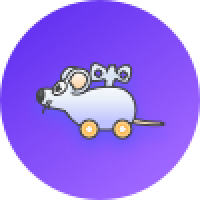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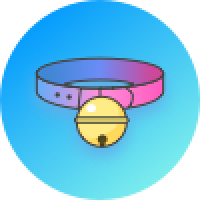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