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百姓,庸庸碌碌。
虽然早出晚归,辛勤耕作,终究是为了一日三餐奔走蹉跎。
百姓之上就是各级官吏,这些人上面领着王室的俸禄,下面辖制着百姓。
而官吏之上就是王室。
一国之主,富有天下,是真正的人上之人,九五之尊。
正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寻常人的眼中,走到这一步就算是登峰造极了。
可谁又知道,王室之上,还有更高的存在。
他们就是,宗派!
不同于世俗江湖中的散修。
真正的宗派掌握着这片天地间最优质的资源,享受着最鼎盛的香火。
它们占据着天地灵气最为充裕的洞天福地,高高在上地控制着整个世俗世界的运行。
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王室更迭,政权交替。
这片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就是他们予取予求的私家猎场。
只是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高,高到在寻常人的认知之外。
宋运和无名要造反,却不是密谋。
落星关不是西顾城。
入夜之后,整座落星关漆黑一片,别说坊市商贾,红男绿女了。
连野狗的叫声都压的低低的。
一座遵从军营号令的城,或者说是伪装成边城的军营吧。
偌大的落星关只有元帅的行营还亮着灯火。
可即便如此,灯火下也是死一样的沉寂。
无名闷着头一杯又一杯,宋运来者不拒,也是如此。
二人沉默的喝着西狄特有的烈酒,这种叫赤焰的酒名副其实。
攻城掠地之时,若有攻不下的城池,赤焰酒便是焚天灭地的火油!
谁都没有说话,宋运麾下的将士们听了一辈子命令,已经懒得揣测元帅的心思。
而无名和宋运则各怀心事。
只有一个白衣文士欲言又止。
“你想好了?”
过了许久,眼看月影都有些倾斜,无名才缓缓开口。
“想了很久了。”宋运本就枯槁的身体熬了半夜,看上去更平添了些油尽灯枯。
“敢想和敢做是两回事,敢做和能做又是两回事。”
无名晃了晃坛中所剩无几的酒,在烛火的掩映下,鬓边的白发分外引人注意。
“你为什么不说最后一句。”
宋运自嘲地笑了笑。
“能做和能做成又是两回事。”
无名没有回答,也没有喝酒,灯火闪动着,映着他瘦削的脸颊。
虽然此刻他的身影看起来有些疲惫甚至是意兴阑珊,可那一对眼睛里的目光却坚定无比。
甚至还隐隐透着点兴奋。
“这么多年,我做过的所有荒唐事都是你撺掇的吧。”
无名歪着头看了看宋运,又问道。
“我们多久没见了,十年?还是二十年?”
“谁知道呢。”宋运轻轻活动了一下筋骨,“我是没脸见你,可是你有脸见我啊!”
“这些年你路过多少次落星关?你是连骂都懒得骂我了吗?”
无名没有搭话,他注视着宋运。
神色复杂。
在场的所有人除了白衣文士好像没人知道,宋运也仅仅比无名大两岁而已。
仅仅两岁,枯槁至此。
“当年的事,你有什么需要和我解释的吗?”
终究是无名开了口。
“解释如何,不解释又如何?纵然有一万个理由和借口,但那件事我还是做了。”
宋运缓缓起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像是用尽了全力。
营帐中所有军人都置若罔闻,可是眼中都有泪滴打转。
当年意气风发,纵横天下的战神啊!
谁能想到会是眼前这般模样。
如果脱下一身帅服,和路边的瘸腿乞丐又有什么区别。
“反正都要死了,就干一场吧。要不我闭不上眼!”
宋运看了看醉成一滩烂泥的陈半生,脸上多了一丝戏谑。
“你做的荒唐事,这件跟我无关。”
无名一愣,紧接着笑了起来。
“荒唐?”
……
月下奔流着黑色的河,漫过江心的沙汀。
陈半生这一觉睡得香甜。
再次睁开眼睛早已日上三竿。
营帐中空无一人,倒是外面的操练声颇为威武。
虽然是宿醉,却不觉得头疼,想来昨天饮的赤焰是上好的佳酿。
饿得半死,陈半生试图着在营帐中翻出一些吃的。
很显然,他的想法是徒劳的。
偌大的营帐除了摆放整齐的盔甲就是明晃晃的刀枪,别说食物,连个老鼠都见不着。
摸了摸瘪瘪的肚子,陈半生开始后悔昨天逞英雄的行为。
放着一桌子酒肉在那里,装个求啊!
要是小安子在那里肯定会二话不说,吃饱肚子再干!
想想自己真够倒霉的,跟着无名这个兜比脸干净的人,还不如在西顾城厮混呢!
“饿了!”
正当陈半生垂头丧气自怨自艾的时候,一张大脸骤然出现在他面前。
“NM!什么东西!”
陈半生被吓得一个激灵。
缓过神来,才发现面前的正是王大柱子。
“去偷鸡吗?”
王大柱子看起来挺喜欢陈半生的,换了别人就冲那句“NM”,不被他打死也得打残。
“什么?”陈半生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西狄的军帐中,宋元帅的行营内。
敌国的先锋大将要带他去。
偷鸡……
“偷鸡……干嘛?”
陈半生有些慌。
“我也饿了……”大柱子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
“养鸡的地方我进不去。”
“就这么窄……”
大柱子比划着宽度,还煞有介事的在陈半生身上比了比。
“你肯定进得去!”
直到陈半生昏头涨脑,莫名其妙地跟着大柱子来到鸡舍前,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确定你会烤!”
陈半生对大柱子有些怀疑,这么大的体格子,到底要去怎样烤一只鸡,这真的是个问题。
“放心!”
大柱子把胸脯拍的山响,一把就把陈半生塞进了鸡舍。
陈半生发誓他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比大柱子更能吃的人。
他一共从鸡舍里偷出了二十只鸡,因为大柱子号称要吃十九只。
二人在元帅行营的假山后架起了火堆,陈半生目瞪口呆的看着大柱子。
看着他极为麻利地处理着那些可怜的芦花鸡,手法极为娴熟。
“你这可以啊,经常干?”
陈半生撕了一只鸡腿,味道还不错。
“第一次干。”
大柱子擦了擦口水,一口就吞下半只。
“为啥,军营里难道没有比我瘦的?”陈半生不解。
“不是,没人敢偷!”大柱子头也不抬,大快朵颐。
“为什么?”陈半生觉得有点不对。
“这些鸡是大帅的宠物,谁敢偷!”大柱子义正辞严。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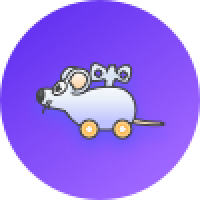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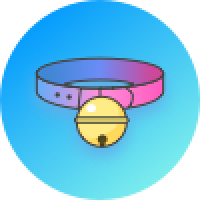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